CZ新專訪全文:從普通程式設計師到華人首富,與FTX的紛擾、進監獄,做慈善、出書,現在的CZ關注什麼?
原文標題:Binance CEO:4 個月監獄,40 億美元罰款,以及接下來將發生什麼
原文作者:All-In Podcast,YouTube
編譯:Peggy,BlockBeats
編者按:這次訪談記錄了全球加密貨幣行業最具影響力也最具爭議的人物——CZ(趙長鵬)從巔峰、入獄到重生的完整心路歷程。
打破了外界對百億巨頭的神話想像,展現了一個極其真實且帶有極簡主義色彩的普通人:他在麥當勞翻過肉餅,在彭博寫過底層代碼,甚至在財富自由後依然習慣訂經濟艙。最令人震撼的除了 Binance 的崛起,還有他首次詳盡披露了與政府司法部博弈的細節,在面臨長達數周的心理戰、媒體渲染下的勒索風險,以及西雅圖監獄裡複雜的種族幫派規則時,他是如何保持情緒的絕對穩定。
CZ 坦誠地回顧了與 SBF 的恩怨始末,以及被迫離開 Binance 管理層時那次的痛哭。如今,他轉身投入到不設代幣、純粹公益的全球教育事業。這不僅是一部加密行業的編年史,更是一次關於權力、金錢與自由邊界的深刻自省。

看點
· 從中國到加拿大的早年經歷
· CZ 的早期職業經歷:出奇地「普通」
· 在上海創辦第一家公司
· 與比特幣結緣
· 全倉押注加密行業
· 為何創立 Binance?
· FTX 事件始末:與 SBF 的關係及其崩盤
· 直面拜登政府「反加密」的司法部
· 聯邦監獄內部生活是什麼樣?
· 離開 Binance 後的生活與新事業
以下為播客全部對談內容:
從中國到加拿大的早年經歷
Chamath:CZ,歡迎來到《All-In》播客。我想把時間線拉回到最開始,因為我覺得很多人並不了解你的背景,至少沒有他們應該了解的那麼多。你早年在加拿大的一段經歷跟我很像,這部分我特別在意。你在麥當勞打過工,我在漢堡王打過工。
CZ:My father went to Canada to study in 1984.
Chamath:How did he get that opportunity? Did he stay in Canada after that?
CZ:He would come back to see us, maybe once or twice a year, but most of the time he was in Canada.
Chamath:Was he a teacher in China?
CZ:He was a teacher, a professor. He first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for an exchange program, and then after a few years, he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in Vancouver. Later, we also started applying to go there, but at that time, getting a passport was very difficult, it took three to four years to get it. We started applying around 1985, and it took about two to three years to get the passport.
Chamath:Are you saying you got a Chinese passport?
CZ:Yes, a Chinese passport. And then it took several more years to get the visa, the process was very slow back then.
Chamath:How did it feel to move to Vancouver?
CZ:Completely different, like arriving in a whole new country. I had studied English for one or two years in school in China, but I was not fluent at all. However, Vancouver was great, you know, Canada, good greenery, open spaces, everywhere was pretty, the standard of living was high, everything was clean. The fruits were also bigger. The overall environment was very comfortable.
Chamath:After the family reunion, did your parents both work?
CZ:My dad wa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earning about 1000 Canadian dollars a month. The school also provided very cheap teacher housing, so we lived on campus.
On the third day after we arrived in Canada, my mom went to work at a clothing factory, sewing and stitching clothes. She had taught math and history in China, but her English was not very good, so she could not find a job at the same level and could only work in the factory for the lowest wages. She worked there for seven to ten years, just doing that.
Chamath:My mom was a nurse in Sri Lanka, and after we immigrated and obtained refugee status, my father couldn't find a job. My mom went to work as a housekeeper to make a living. Later, she went back to work as a nurse's assistant. I think I was around 14 when I received my first paycheck.
CZ's Early Career Experience: Surprisingly "Ordinary"
CZ:Yes, that's right. I also got my first job at around 14 or 15, working at McDonald's.
Chamath:我們同歲,那估計也是 14 歲。你還記得當時卑詩省的最低時薪是多少嗎?
CZ:記得,那時候最低工資是 6 加元。
Chamath:這太不可思議了,安大略省那時候 4.55 加元。
CZ:但在麥當勞,他們只付 4.5 加元。這比法定最低工資還低,因為麥當勞當時似乎有一項特殊豁免權,畢竟那裡雇了很多年輕人。我記得是在 14 歲生日那天去申請的,一周後我就在那兒翻肉餅了,那是我人生第一筆收入。
Chamath:那你當時算不算那種早熟的「技術神童」?就是那種 24 小時都在寫代碼、鑽研計算機科學的小孩?
CZ:不,我覺得我稱不上那種人。我是個技術控,大學讀的計算機,高中就開始對編程感興趣並自學了,但我絕對不是什麼編程奇才。算是個還不錯的程序員吧,職業生涯裡也寫過一些像樣的代碼。但在我 28 到 30 歲左右的時候,開始脫離代碼層,去做更多的業務拓展和銷售之類的工作了。
Chamath:你當時朋友多嗎?
CZ:挺多的。
Chamath:只有亞裔朋友嗎?還是各色人種都有?
CZ:都有。其實亞裔和非亞裔的朋友我都有,但在我們學校,大多數亞洲孩子只跟亞洲孩子扎堆,我算是個例外,我也有不少白人朋友,有各種各樣的朋友圈子。我在加拿大的青少年時光非常棒,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幾年。我覺得正是那段時光塑造了我樂觀的性格,我通常是個挺快樂的人。
Chamath:當你沒考上我的母校滑鐵盧大學,只能屈就麥吉爾大學的時候,你心裡是什麼滋味?會覺得自己很笨嗎?
CZ:這個嘛,其實當時我在滑鐵盧、麥吉爾還有多倫多大學之間紆絆。但我知道我肯定不去卑詩大學,因為我想換個城市。其實 UBC 給了我錄取,但我就是不想去。當時我一位非常尊敬的長輩建議說,你應該去當醫生,因為醫生的生活體面,薪水也高。我聽了她的建議,選擇了生物學。而滑鐵盧大學並不是以生物見長的,對吧?所以我去了麥吉爾。但讀了一個學期後,我就對自己說:不學生物了,我要轉到計算機科學。
Chamath:那是典型的大學生活嗎?暑假有沒有找到很牛的工作?還是像普通的大學生一樣,得為了交學費奔波?
CZ:我每個暑假都工作,而且我在學年期間也會打兼職。
Chamath:所以沒有債?你當時是不是想:我一定要在沒有任何債務的情況下畢業?
CZ:對,第一年我沒申請助學貸款。其實我還是從我爸那兒拿了 6,000 加元。第二年錢還是不夠,我姐姐給了我 3,000 加元。從那以後,我就再也沒跟家裡要過一分錢了,完全自給自足。所以很幸運,我沒有任何學生債務,但這都是靠每個夏天不停打工換來的。
Chamath:你知道滑鐵盧大學最棒、也是最救命的一點是什麼嗎?就是它的實習計畫,我當時找到了幾份非常棒的實習工作。即便如此,我畢業時還是背了大約 3 萬加元的債,不過我那時候在股票交易上表現挺活躍的。
後來我的老闆,一個叫麥克·費舍爾的人,對我做了一件極其慷慨的事。我當時在一家銀行做衍生品交易員,那是我的正職,但我私下也炒股,還幫他賺了不少錢。他問:「你欠了多少債?」我說大概 3 萬,準確說是 3 萬 2。他說:「現在就下樓去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把你的債還清,我給你寫支票。」
CZ:哇。
Chamath:他當場給我寫了一張 3.2 萬加元的支票。
CZ:你應該跟他說欠了 3.3 萬,或者 30 萬。
Chamath:這就是加拿大不可思議的地方,你能接受極好的教育,而且不會被那種讓你翻不了身的債務壓死,這在美國對很多人來說已經是不可能的事了。
CZ:即便在麥吉爾,也有很多從美國跑來讀書的人,他們付著國際生的學費,卻發現還是比在美國讀書便宜。我當時覺得這太瘋狂了。所以我們真的很幸運,加拿大的學費還算合理。
Chamath:所以你從麥吉爾的計算機系畢業後做了什麼?
CZ:哦,其實我沒從麥吉爾畢業。我在那兒讀了四年,大三那年我找到了一份實習,大四那年實習期延長了,我就沒回麥吉爾。所以我並沒有麥吉爾的學位。
後來我發現我去日本申請工作簽證需要一個學士學位。當時正值 2000 年左右互聯網泡沫的頂峰,我就參加了一個叫「美國計算機科學學院」的線上教育項目,在那兒拿到了學位。
Chamath:我的天!所以名義上你是那所學校的畢業生?
CZ:名義上是的。
Chamath:好吧,那你當時是拿到了哪份實習,讓你決定直接在那兒幹了?
CZ:是在東京的一份實習,從大一開始,我就一直在做編程相關的活兒。我在一家叫 Original SIM 的公司寫過模擬軟體。大三的時候,我進了東京的一家公司,叫 Fusion Systems Japan。他們在為東京證券交易平台的經紀商開發訂單執行系統。
Chamath:那是一家在蒙特婁或加拿大有辦公室的日本公司嗎?
CZ:不,我直接飛去了東京。
Chamath:你去了東京?
CZ:對,其實那是一家由幾個美國人在東京開的公司。
Chamath:所以你當時覺得這像是一場冒險,我要去東京過個暑假。
CZ:你想啊,我當時只是個大學生。能去東京生活簡直跟做夢一樣。
Chamath:那你當時主要負責哪類軟體的開發?
CZ:主要是訂單執行軟體。簡單來說,就是負責處理和傳輸交易指令的系統。
Chamath:類似於如今支撐 Binance 業務的那種底層邏輯嗎?
CZ:基本可以這樣理解,架構風格很接近。不過,我參與開發的所有軟體都不涉及決策演算法,它們只負責高效地執行指令。
Chamath:當你初次接觸這個領域時,你的反應是「天呐,我太熱愛這個了」,還是僅僅覺得「既然接到了程式任務,我理解其邏輯,那就把它完成」?你是被業務本身吸引,還是僅僅把它當成一份工作?
CZ:起初純粹是當作一份工作。那時我太年輕,對各行各業缺乏宏觀的認知。剛進公司時,我被分派去開發一個數位影像存儲系統,它並非像 iPhone 相簿那樣簡單,而是用於醫療影像的專業系統。
但不久後,公司的核心業務轉向了訂單執行系統,我也隨之參與其中。這成為了我職業生涯的重心。我之所以喜歡它,是因為它對技術專業性要求極高。這個領域的核心是效率:極致的響應速度和超低的延遲。這種對效率的追求在潛意識裡非常契合我的性格。
Chamath:深入探討一下,像 Jump 這種高頻交易機構,他們為了優化效率和延遲幾乎不計代價,甚至會自研電路斷路器和物理光纖基礎設施,只為節省幾毫秒。在軟件層面,這種極致的優化是如何体現的?在編寫代碼時,你如何處理這些極限邊界條件?
CZ:這分為多個層面。首先是軟件架構的優化,你必須確保系統絕對高效。例如,為了消除延遲,我們會剔除所有的數據庫查詢,將一切操作移至內存進行。同時要精簡計算邏輯,尤其是針對下單前和交易前的風險審查流程。更高級的階段會涉及到硬件層面,比如使用現場可編程門陣列,這是一種集成在網卡上的可編程晶片。
Chamath:這樣數據就不必在內存和處理器之間來回往返,從而進一步提升速度。
CZ:沒錯。大約十年前我還在寫代碼時,一次數據往返大約需要 100 微秒;而通過硬件優化,可以將延遲降至 20 微秒。之後就是物理設施的優化,比如尋求伺服器託管,儘量縮短物理距離。
Chamath:這讓我想起 AI 領域的 Groq。我們十年前初創時也有類似的洞察,讓數據在 GPU 和 HBM(高帶寬顯存)之間穿梭是非常低效的。所以我們決定採用 SRAM,將一切數據保留在晶片上。
這種思路在推理的解碼階段非常有效。既然高頻交易涉及如此巨額的資金,為什麼這些機構沒有嘗試研發定制化的專用集成電路(ASIC)?我理解 FPGA 的應用,但似乎沒人走到自研特定芯片(ASIC)這一步,還是說他們做了但秘而不宣?
CZ:我認為這種規模的芯片定制並不普及,主要原因在於算法迭代太快。雖然芯片化設計非常高效,但一旦需要修改邏輯,研發周期太長。相比之下,FPGA 在性能與可重構性之間取得了最佳平衡。即便如此,FPGA 的編程周期依然比純軟件要長出十倍。
Chamath:你在日本工作的公司後來成功了嗎?
CZ:相當成功。就在 2000 年互聯網泡沫破裂前夕,那家公司被一家納斯達克上市公司收購了。
Chamath:收購金額很大嗎?
CZ:當時大約是 5200 萬美元。在那個時代,這算是一筆巨款。
Chamath:那是你察覺到商機、決定投身創業的契機嗎?還是另有隱情?
CZ:不,那時我才二十出頭,還太年輕。在公司裡,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程序員,用日語說就是一名上班族。
Chamath:明白。那在那之後發生了什麼?
CZ:公司被收購後,母公司與原團隊之間出現了嚴重的文化衝突,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企業併購可能面臨的困境。管理層不合,於是原合夥人決定另立門戶,成立了另一家公司。
雖然我沒從那次收購中分到錢,但合夥人們賺了不少。他們租下了極其豪華的辦公室,然而新公司只維持了一年。這證明了過去的成功並不代表未來的必然,甚至可能產生誤導。他們揮金如土,卻沒有營收,公司在 2001 年便倒閉了。2001 年初,我開始尋找新機會,恰好彭博在招聘。那是在「9·11」事件發生前,我拿到了錄用通知,但還沒正式入職。
Chamath:岗位是在哪裡,紐約嗎?
CZ:當時我還在東京,但岗位是在紐約。「9·11」發生後,我致電彭博詢問職位是否還有效,是否還要我去。他們反問我:「你還敢來嗎?」我說:「沒問題。」於是,我在 2001 年 11 月抵達了紐約。
Chamath:當時的氛圍如何?
CZ:街上冷冷清清,但我適應得不錯。紐約雖然沉寂了幾個月,但很快就恢復了往日的活力,對我來說沒有太大困擾,我在彭博工作了四年。
Chamath:那期間你是否依然扮演著打工人的角色?在大型企業工作,拿著薪水、獎金,或許還有一些期權。
CZ:是的,我當時以高級開發人員的身份入職,被分配到了「Tradebook Futures」團隊。那是他們新成立的部門,旨在整合並開發彭博終端上的期貨交易系統。
Chamath:那時候還沒有創業的念頭嗎?
CZ:確實沒有。
Chamath:那你當時追求的是什麼?穩定嗎?為什麼選擇在紐約的彭博工作?
CZ:當時我只有 24、25 歲,只是個想找份好工作、體驗不同世界、探索人生方向的年輕人。我深知自己當時缺乏獨立創業的經驗。在東京時,公司只有 200 人左右,而當時的彭博已有約 3,000 名員工。
對我而言,那已經是龐然大物了:辦公室極其華麗,有魚缸,還有免費食物。入職後我遇到了很好的上司,兩年內晉升了三次。最後我開始帶領一個從 60 人增長到 80 人的團隊。那是我的職業轉折點。我不再編寫代碼,轉而進入管理崗位。對我來說,那是職業生涯中最為艱難的一次轉型。
在上海創辦第一家公司
Chamath:隨後你離職去了中國?這又是如何發生的?
CZ:2005 年初,我在日本工作時的那些老同事計劃創辦一家新的金融科技公司。他們當時都在亞洲,在東京、上海和香港之間猶豫。由於認為上海是未來金融科技發展最具潛力的城市,我們選了上海,雖然後來證明香港當時的業務機會其實更多。2005 年我搬到了上海。創始團隊共有六個人:四名白人、一名日本人和我。我是唯一能說中文的人,儘管那時我的中文也有些生疏。
Chamath:你們幾個人就這樣空降上海了,當時的業務設想是什麼?
CZ:我們認為自己擁有華爾街最前沿的交易技術經驗。
Chamath:你的那些朋友後來也去了紐約嗎?還是留在日本?
CZ:其中兩個當時隨我在紐約,另外三個留在日本。我們六個人匯合,初衷是把華爾街的交易技術引入中國,為中國的經紀商和交易平台提供服務。於是,團隊又租下了一間非常豪華的辦公室……
Chamath:等等,這是你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創業。你當時懂得詢問股權分配或股權結構表這類問題嗎?還是只是盲目參與?
CZ:分配並不完全均等。核心負責人持有約 39% 到 40%,我們其餘五人平分剩餘股份,我持有約 11%。我當時只知道這個比例,但對於股東權益、優先股與普通股的區別等法律細節,我一竅不通。
Chamath:So you moved to Shanghai with this 11% stake.
CZ:Yes, I had no idea about it, just pure enthusiasm. As a junior partner, because I could speak Chinese, I was responsible for communicating with potential clients in Shanghai. After contacting domestic brokers, I discovered a fatal issue: we registered as a wholly foreign-owned enterprise, but the policy at that time did not allow domestic brokers 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cooperate with such companies. It was only after the company was established that we realized this. So we had to pivot. To survive, we started taking on various IT outsourcing projects.
Chamath:Did you become a consulting firm like Deloitte?
CZ:Even worse than Deloitte. We took on all kinds of tasks: fixing printers, implementing SAP systems, and so on, with a very broad scope of business. We persisted like this for several years. Surprisingly, we really survived on these tasks and accumulated a large number of clients i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such as SAIC Motor, Shanghai Volkswagen, and FAW Group. About three to four years later, we opened an office in Hong Kong and started dealing with international giants such as Morgan Stanley, Deutsche Bank, and Credit Suisse.
Chamath:So the business eventually took off.
CZ:Yes, that company still exists today. I stayed there for eight years until I left in 2013.
Chamath:Did you stay in Shanghai during those eight years?
CZ:Mainly in Shanghai. But I also spent a lot of time setting up the Hong Kong office and often went to Tokyo to serve clients there.
Chamath:How big did the company grow later on?
CZ:As far as I know, the company grew to about 200 people and maintained that size for a long time.
Chamath:As a junior partner, were you directly involved in profit sharing?
CZ:In fact, we didn't get a lot of profit sharing. I reinvested most of my savings back into the company and never cashed out a penny. However, after a few years, the company's revenue was enough to support high salaries for the partners. By then, I had a family, my children were attending international schools, and my annual salary had reached six figures.
Chamath:Were you married during that time?
CZ:Yes, I got married while working in New York.
Chamath:How did you meet your ex-wife?
CZ:我第一次去東京實習時就認識了她。大約是 1999 年。後來她去紐約找我,我們結婚生子。雖然現在我們已經分開了,但在上海的那段日子,薪水足以讓孩子接受良好的國際學校教育,這對我來說已經很滿足了。
Chamath:回顧你之前的經歷,依然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你即將去創立 Binance。
CZ:完全沒有,當時我對此還一無所知。
Chamath:那是 2013 到 2014 年間,你當時多大?大概 36 歲左右?
CZ:2013 年時,我剛好 36 歲。
與比特幣結緣
Chamath:正值而立之年。你當時還是個拿薪水的上班族,是那家公司的初級合夥人,事業有成,孩子也都在私立學校就讀。那麼,接下來發生了什麼?
CZ:我接觸到了比特幣。起初是朋友向我推薦,讓我關注一下這個叫比特幣的東西。我花了大約六個月的時間才真正理解它的本質,那大概是從 2013 年 7 月開始的。
Chamath:是因為你讀了那篇白皮書,然後發現需要反覆研讀才能領會嗎?
CZ:基本如此。而且當時主要的交流陣地是 BitcoinTalk.org 論壇,我幾乎翻遍了上面的所有內容。
Chamath:你讀過我 2012 年在彭博發表的那篇文章嗎?它對你產生過影響嗎?
CZ:坦白說,我不記得了。我當時讀了海量的資料,確實很難想起具體的出處。
Chamath:開個玩笑,不過我確實寫過。有趣的是,我當時和邁克爾·彭博關係不錯,他雖然輩分很高,算不上我的導師,但他很賞識我。2012 年左右,他的團隊邀請我寫一篇專欄文章。我在文中建議每個人都應該將淨資產的 1% 投入比特幣,將其作為一種保險。
文章在彭博終端發布後,我對比特幣產生了一種覺醒式的認知。它是我見過的最令人著迷的技術產品。最令我折服的一點——不知道你是否也有同感——它是唯一一篇我從頭讀到尾,並感歎其文字之優雅的非技術性散文。它並不像那些只寫給博士看的晦澀文獻,你完全可以把它交給任何一個不懂技術的人看,他們也能讀懂。
CZ:而且全文只有區區九頁。
Chamath:沒錯。要把複雜的邏輯寫得如此精煉,需要極高的智慧。
CZ:言簡意醇比長篇大論難得多。如果讓別人來重寫這篇白皮書,恐怕得寫上 90 頁。
Chamath:向你介紹比特幣的那位朋友是誰?是你當時的同事,還是在上海結識的朋友?
CZ:是我的一個朋友,叫曹大容(Ron Cao)。我們沒有業務往來,他當時是光速創投(Light Speed Ventures)中國的董事總經理。我們常在一起玩撲克牌,那是那種小賭怡情的私宅牌局,參與者要麼是正在打拼的創業者,要麼是風險投資人。
在一次牌局上,大容建議我關注比特幣。隨後我們進行了深入交流,當時還在沃爾瑪工作的李啟元(Bobby Lee)也準備辭職去擔任比特幣中國(BTCZ)的 CEO。
作為交易的一部分,大容代表光速創投投資了 BTCZ。那是 2013 年 7 月。看到他們兩人對此如此嚴肅對待,我第二天便約了 Bobby 吃午餐。Bobby 建議我將淨資產的 10% 投入比特幣,他的理由是:即便歸零,你只損失 10%;但如果漲了 10 倍,你的淨資產就能翻倍。這聽起來非常有說服力。於是我開始鑽研,直到 2013 年底我才徹底確信其價值。但尷尬的是,比特幣在 2013 年半年內從 70 美元飆升到了 1000 美元。
Chamath:眼睜睜看著它漲了 15 倍,你當時是什麼心情?
CZ:我覺得自己錯過了最佳時機。因為在比特幣行業,無論你何時入場,你永遠會覺得自己來晚了,因為你接觸到的每個人似乎都比你早。
Chamath:在你鑽研期間,有可以交流的圈子嗎?
CZ:上海當時有一個非常小的社區。我當時幾乎和世界上任何願意聊比特幣的人溝通。我在台灣也有幾個在台積電工作的朋友,他們當時正辭職嘗試開發比特幣礦機晶片。此外還有一些礦工,比如圈內人稱「七彩神仙魚」(毛世行)的大佬,他是 F2Pool 魚池的創始人。
他們當時在杭州,我們會約在上海見面交流。最關鍵的轉折點是 2013 年 12 月在拉斯維加斯舉行的比特幣大會。我飛過去見到了行業內的所有人。
那是一場只有 200 人的小型會議,Vitalik(以太坊創始人)、查理·李(萊特幣創始人)等如今的巨頭當時都在場。當時正值「絲綢之路」網站被查,媒體渲染比特幣只是毒梟的工具。但在會議現場,我看到的是一群非常有禮貌的技術極客和年輕人。當你和 Vitalik 交流時,你會發現他是一個非常單純、善良的人。
Chamath:你做這些事的時候還在原來的公司任職嗎?你直接告訴合夥人要去拉斯維加斯玩幾天?
CZ:是的。回來後,我向合夥人建議公司應該開發比特幣支付系統。當時 Bitpay 剛剛完成了 400 萬美元的融資,是行業內的領頭羊。
Chamath:提到 Bitpay,我有個很有趣的亲身經歷。我當時急於證明比特幣的交易能力,在 2012 或 2013 年,我通過 Bitpay 用比特幣買了一輛路虎。按現在的幣價折算,那輛車大概價值 9000 萬美元。更離譜的是,我還用比特幣在塔霍湖買了一塊地,只是為了證明房地產交易的可行性。現在回想起來,那塊地相當於 10 億美元。
Chamath:帳不能這麼算。即便你當時不用比特幣,你也會用等額的現金去買。而那筆現金本可以用來買入更多的比特幣。這本質上是心理帳戶的問題。
Chamath:回到正題,你向合夥人提議做 Bitpay 的競品,他們顯然無法理解。那時你買入比特幣了嗎?
CZ:當時我只買了一個幣試試。
全倉押注加密行業
Chamath:那後來呢?
CZ:我告訴合夥人們,這是我一生中見到的最大機會。我這輩子見證了三個底層的技術變革:互聯網(當時我太年輕沒能深度參與)、比特幣,以及後來的 AI。當時我 36 歲,我不想再錯過比特幣。我決定辭職全身心投入這個行業。
為了籌集資金,我決定賣掉上海的房產。賣房花了幾個月時間,最終賣了約 90 萬美元。我全家搬到了東京的租住房裡,我則頻繁往返於上海和東京之間。房款是分批到賬的。第一筆資金到賬時幣價是 800 美元,隨後一路下跌。我在 600 美元、400 美元的時候持續補倉,最終持倉均價大約在 600 美元左右。
Chamath:房款全換成了比特幣,但你當時還沒有工作。
CZ:我同時在找工作,而且目標非常明確,只看比特幣行業。從我決定辭職到敲定新工作,只花了不到三週時間。
Chamath:誰雇用了你?
CZ:起初我和 BTCZ 的 Bobby 談過,他想招募我。但隨後 Blockchain.info(現在的 Blockchain.com)的 Roger Ver 找到了我。當時他們團隊只有三個人:創始人 Ben Reeves、剛入職的 CEO Nicholas Cary,我是第三個。
我擔任技術副總裁(VP of Engineering)。我飛往英國倫敦北部的約克工作了一段時間。但那段經歷並不順利,團隊擴張到 18 人後,新任 CFO Peter Smith 為了融資調整了管理架構,導致公司文化發生劇劇變。很多開發人員包括我都選擇了離開。我在那裡只待了大約六七個月,雖然時間不長,但那段經歷讓我受益匪淺。
Chamath:學會哪些事千萬別做。
CZ:也算是。加入 Blockchain.info 時,Ben Reeves 就說過,你看,我們沒有公司、沒有辦公室,所有人都遠程辦公;我們用比特幣給每個人發工資。這些做法讓我學到不少東西。直到今天,這種理念在 Binance 內部仍然被大量採用。
我學到的另一點是,當時 Blockchain.info 是行業裡最大的用戶平台之一,錢包數量大約有 200 萬,甚至一度超過 Coinbase。
可他們幾乎沒有所謂市場部打法,整個營銷基本就靠 BitcoinTalk.org 上的一條帖子。帖子長達 150 頁,Ben Reeves 就在裡面不斷回覆、持續互動,平台用戶就這樣一路增長到 200 萬。那讓我意識到,只要方法得當,靠很「游擊式」的營銷也能做出規模。我從那家公司學到了很多,但後來企業文化發生了一些變化,不再適合我,我就離開了。之後是何一把我招進了 OKCoin。
Chamath:做開發?
CZ:擔任 CTO。在這個過程中,我覺得 BTC China 又幫了我一次。因為我離開後又在找工作,何一正好在跟我聊這件事,Bobby Lee 聽說後也聯絡了我。那時候 OKCoin 開出的條件是 5% 的股權;隨後 BTC China 過來直接給到 10%。結果 OKCoin 在三小時內就把條件追平了。
我當時在上海和北京之間猶豫,最後決定去北京加入 OKCoin。那會兒何一自己只有 1% 的股權,他招我進去,某種意義上是希望我成為更重要的合夥人——承擔更大的業務責任。我在 OKCoin 待了大約八個月,但同樣沒有堅持太久。
Chamath:為什麼?
CZ:主要還是文化和價值觀的不一致,有些做法我無法認同。舉個很簡單的例子:他們做活動、做手續費折扣宣傳時,廣告寫得像是人人都能享受,但實際上你得主動去申請才會給你,並不是自動生效,類似這種細節讓我不舒服。於是到 2015 年初,我決定離開。大致就是這樣,主要是在 2014 年那幾個月,延續到 2015 年初。
為何創立 Binance?
Chamath:那後來怎麼就做了 Binance?
CZ:2015 年,我和幾個以前的同事決定在日本東京做一家比特幣交易平台。因為那是 Mt. Gox 事件之後一年,日本市場出現了明顯的真空。
就在我決定離開 OKCoin 的同一天,有兩位開發者找到我,他們也剛好各自辭職。我說那不如我們三個人一起做點事。我們當時約定我來當 CEO、拿更多股權,負責融資;我用自己的積蓄給兩位開發者發工資,而我自己不拿薪水。
我們很快做出一個演示版本,下載了一個開源交易平台系統,把介面稍微改得更好看一些。
Chamath:所以 Binance 就是從套開源項目開始的?
CZ:不是(笑)。那還在 Binance 之前,我們也沒有對外這麼說。我當時非常坦誠,這個 Demo 只是我們兩三天內趕出來的概念驗證,用來展示方向,不是最終產品。
另外,我們寫了一個腳本去抓取 Bitfinex 的行情數據。Bitfinex 當時是大型交易平台之一,我們相當於複製了它的訂單簿,讓介面上不斷閃動成交、看起來很活躍,投資人看到後會覺得技術很強。
但更關鍵的是,當他們提問時,我能把問題講得很深,比如如何把撮合做快、如何做內存撮合引擎、資料庫結構怎麼設計等等,這些都是我之前積累下來的。
Chamath:也就是你把你學到的那些內存撮合、資料庫全都講出來了。
CZ:對。我能深入回答他們的技術問題,所以他們相信這不只是一個好看的 Demo。但他們也指出你們在日本做交易平台不一定能成功,你不會日語。於是他們建議為什麼不把這套交易系統賣給別的交易平台?因為很多日本交易平台的技術並不強。
我覺得可行,就去談了幾家。大概兩週後,我們就和其中一家簽了合同,對方以 36 萬美元買下這套系統,先付了 18 萬美元的首付款。那筆錢足夠讓我不再用個人存款發薪水,我當然鬆了一口氣。於是我們從做自己的交易平台轉向做交易系統供應商。
Chamath:也就是賣軟體。
CZ:對,賣軟體。到 2015 年 7 月,有一批中國公司也找上門來,說他們也想買系統。
Chamath:不好意思打斷一下,但這段經歷太驚人了。很多創業故事裡,當別人問「你公司做得怎麼樣、值多少錢」時,大家總會聯想到那種「靈光一現、命中注定」的傳奇。
比如 Binance 現在大概是 2000 億美元級別,很多人以為這種公司一定有個特別炸裂的起點。可你的經歷更像真實創業:一路摸索、學習、試錯、迭代,路徑並不直觀,直到某個時刻才發生催化。即便如此,你當時做的也不是一個終局形態,而是在做授權、做服務。很多人誤解了創業的本質,它更多是韌性,是把苦活累活一遍遍做下去的耐力。
CZ:完全同意。很多人會把創業浪漫化,覺得一開始就天降靈感。
Chamath:像 Facebook 的故事,大學裡隨手一寫,突然就百萬用戶。
CZ:是的,Facebook、微軟、谷歌這類故事最容易被傳播,車庫、宿舍、從零到一飛起來。
Chamath:但現實裡,尤其是金融、或者像特斯拉這種公司,更多是漫長的苦戰。
CZ:沒錯,是持續的苦戰。你得反覆嘗試很多方向,開始時根本看不出哪條路會通。那三家更像是極少數從第一天就對了的例外,但它們塑造了大眾對創業的想象。事實上,99% 甚至 99.9% 的成功公司都不是那種路徑。
所以回到我們當時,軟件授權這門生意做得不錯,我們總共服務了大約 30 家交易平台客戶。
Chamath:等等,真的假的?
CZ:真的,持續了兩年左右。兩年裡我們簽了很多客戶,那其實是個數百萬美元級的授權業務。它也可以算 SaaS,我們稱之為「Exchange as a Service」,按月收固定服務費。業務非常穩定,每增加一個客戶,收入就臺階式上升。這其實是個很好的商業模式。
但到了 2017 年 3 月,中國政府關停了我們的大部分客戶。到 5 月,我們發現必須轉型。
Chamath:但他們沒有直接影響你們,因為你們只是軟件供應商。
CZ:對,我們只是軟件供應商,不運營交易平台,不觸碰業務本身。但問題是客戶沒了,業務就沒了。所以 4 月、5 月我們一直在想怎麼轉型。
那段時間也發生了很多嘗試,比如有三位跟著我幹的同事想做一個 Poloniex 的複製版,Poloniex 當時是最大的交易平台之一。我說我們手上有現金,可以投;但三天後,他們又想做鏈上聊天室、鏈上交易那類軟件,我就覺得不值得再投。
最後我說,既然我們已經有交易系統,為什麼不自己做一個只做幣幣交易的交易平台?系統需要做些定制,但基礎都在。於是 5 月底我們定了,重新做交易平台,做純幣幣交易。
Chamath:當時團隊多大?
CZ:20 人左右,技術人員齊全,但幾乎沒有市場團隊,因為我們原先是 B2B,主要靠銷售。我們只有兩個銷售加上我。決定轉型後,我們說那就自己跑起來:做一家幣幣交易平台。
然後 6 月 1 日到 6 月 10 日,BTC-e 的聯合創始人 Vinnik,在中國做了一次 IC0,10 天募了 1500 萬美元。我看到後非常震驚,他只有一份白皮書和一個網站,沒有產品、什麼都沒有,就能募到 1500 萬。那我想如果他能做到,我也許也能做到。
Chamath:What you need is venture capital. You're thinking that if you get $15 million, you can expand the team, invest in marketing, get the company on a growth trajectory, and not have to worry so much about cash flow pressure.
CZ:Right. Initially, we did plan to go for VC funding, but after seeing that, I realized how efficient an ICO was. In mid-June 2017, I attended a conference where everyone was talking about ICOs. Everyone was telling me, "CZ, you have to do an ICO."
Around June 14th, I made up my mind to gather the team together. We were going to do an ICO and write a whitepaper immediately.
Chamath:Were you already well-known in the Bitcoin or crypto community at that time? Whether in China, Japan, or elsewhere?
CZ:A little bit. I was already somewhat known when I was at Blockchain.info. Blockchain.info was the most popular platform at the time, and I was also the CTO of OKCoin. I was quite active on social media and in charge of their international markets, mainly non-Chinese markets because almost no one on the team spoke English better than I did, even though my English was not that great. So I had some visibility in the community, and people more or less knew who I was.
Chamath:Because you were going to do an ICO, you needed to have some level of fame or endorsement, right?
CZ:Yes. This was also an advantage of being early in the industry. Back then, when you attended a few conferences with only about two hundred participants, no one knew you the first time. But the second time, some people started to remember you. By the third time, others would consider you an insider and even think of you as an expert. During that time, I did build up some reputation.
I also noticed that the person in China who did the ICO at that time, Vinnik, was well-known domestically but not internationally. I had some exposure in both China and internationally. So I judged that I probably had a good chance of doing an ICO and raising a similar amount. Later on, it turned out that we did achieve that.
Chamath:I've always been confused, and still am today, about who the buyers were in your ICO.
CZ:To be honest, even today, it's hard for me to give a completely accurate picture.
Chamath:Were they Chinese? Japanese? Or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ho knew you early on? Or was it because your whitepaper was particularly well-written?
CZ:In terms of investor composition, perhaps 80% to 90% were Chinese, with some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participating as well. The data indicates that around 20,000 people participated in that ICO.
Chamath:兩萬人?
CZ:對,約兩萬人。對一個全新品牌來說,真正的背書其實也就只有兩點:少數人認識我,以及我們把事情講清楚了。
Chamath:所以即便中國當時把交易平台清出市場,IC0 依然被允許?
CZ:需要澄清一下,那時候 IC0 還沒有被明確禁止。
Chamath:對,當時還沒禁,但也談不上被允許。
CZ:嚴格說,是未被批准,處於灰色地帶。再補充一個關鍵背景,我們當時服務的交易平台客戶,主要是「法幣交易平台」,並非純加密交易平台。加密交易平台並不是3 月被叫停的,而是在我們啟動之後才在 9 月迎來監管重拳。我們說的這段時間大概是 2017 年 6、7 月。
Chamath:你當時幾乎是在監管縫隙裡穿針引線。
CZ:確實如此。但我們並不知道政策會在之後落下,只是基於當時的現實做決策。
Chamath:那你們當時賣掉了公司多少股權?
CZ:我們沒有出售股權。我們發行的是代幣,不涉及任何股權安排。我們發行了一個新代幣 BNB,直到今天它仍然存在。我們當時的計劃是售出 60% 的代幣,募集約 1500 萬美元。當然,募集是以比特幣等加密資產計價與結算。
Chamath:你們最初為 BNB 設計的代幣經濟模型是什麼?
CZ:我們提出了若干用途,但最核心、也最能快速落地的一條是持有 BNB 的用戶,在未來交易平台上線後進行交易可以獲得 50% 的手續費折扣,這是最直接的價值承諾。我們同時也提到它未來會演化出自己的鏈,形成一個更完整的生態系統,大概就是三四個主要方向。
Chamath:那你們當時一定很興奮,募集到 1500 萬美元,馬上就能把交易平台做起來。可 9 月政策下來,交易平台本身在中國被禁止了,你們怎麼辦?
CZ:2017 年 9 月 4 日,中國政府多個部門聯合發布文件:第一,虛擬貨幣交易平台不再允許在中國運營;第二,IC0 也不再允許;第三,挖礦同樣被禁止。我們的選擇只有一個:遷出中國。
當時中國仍是重要市場,大約貢獻了 30% 左右的用戶,但我們還有約 70% 的用戶來自全球其他地區。我們判斷即使失去那 30%,業務仍可以生存,甚至仍有不錯的增長空間,於是我提出把團隊搬到東京。
Chamath:你很喜歡東京。
CZ:我對日本並不陌生,至少不是第一次適應一種新文化。
Chamath:而且那時你也會說日語了。
CZ:會一點點,屬於打車級別的日語:會說謝謝、辛苦了、餐廳點菜能看懂一些;壽司的名字我大多能叫出來。大致就是這個水平。但關鍵在於東京對我而言不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城市。那時我們大概 30 人左右,於是決定整體搬遷。
Chamath:所有人都搬了?
CZ:幾乎全部。那是八年前,團隊裡只有一兩個人已婚,幾乎沒人有孩子,所以遷移成本相對低。大家收拾行李就走了。我記得有個產品經理哭了,因為她男朋友還在中國。但她最終還是跟著團隊去了東京,後來也和那位男朋友結了婚,這件事現在回想起來仍然很不可思議。
總之,我們搬到東京之後,平台仍然持續增長。
Chamath:你們最初上線 Binance 時,是一炮而紅嗎?還是需要花很多力氣去找 PMF?早期的病毒傳播是怎麼發生的?流動性又是怎麼建立起來的?
CZ:我會說產品增長得不錯,但代幣價格一度跌破 ICO 價格,跌幅大約 30% 到 40%,大概三周後才恢復。至於 PMF,當時加密市場仍然很熱,我們做的是幣幣交易平台,這不是一個全新的概念,因此需求本身已經存在。
Chamath:那 ICO 就很關鍵了,大家持有代幣,能享受交易手續費折扣,所以會優先選擇 Binance,對嗎?但你們的系統架構是不是也明顯更好?速度更快、穩定性更強?
CZ:是的,系統性能確實顯著更優。那時候甚至不需要複雜對比,只憑直覺體驗就能看出來,在 Binance 下單、撮合的速度明顯快過競爭對手,整個交易系統的性能優勢非常突出。
Chamath:2017 年你們主要在和哪些平台競爭?
CZ:當時 Poloniex、Bittrex 是最大的兩家。中國市場上還有火幣、OKCoin 等,西方市場則有 Coinbase。Gemini 那時候還沒起來,是後來才出現的。Bitstamp、Bitfinex 當時也在,但現在相對小很多。
Chamath:那時候你已經接近 40 歲了,這件事真的開始跑起來,你怎麼消化這種成功?你會不會對自己說這到底發生了什麼?這是真的嗎?
CZ:確實有一些非常不真實的時刻。比如財務同事跟我說,我們這段時間的收入大概是幾百個比特幣,我第一反應是難以置信,這怎麼可能?我們真的賺到這麼多嗎?你確定嗎?對方說確定。於是我們反覆核對、三次核對,還是同一個結果,那種感覺非常震撼。
還有一段時間是 BNB 在恢復價格的那三周,BNB 我們 ICO 定價大概是 0.10 美元,跌到 0.06 美元左右;隨後又開始反彈。那一陣子幾乎是睡一覺醒來漲 20%,開個會回來又漲 20%,甚至去趟洗手間回來也像又漲了一截。當然這是誇張的說法,但節奏確實快得令人眩暈。
Chamath:那種時候你很快就會意識到,等一下,我好像變得很有錢了。
CZ:財富感的衝擊來得更晚一些。大概在 2018 年初,過了六七個月,Forbes 把我放上了封面。那一刻我才真正開始意識到,也許事情已經完全不同了。
Chamath:他們當時怎麼聯繫到你,要做封面?
CZ:我其實也不太清楚具體過程。Forbes 當時在做一期加密主題特刊,找了很多圈內人。他們通過我們的公關團隊聯繫,當時 PR 團隊大概四五個人,說想給我做專訪、拍攝。
我一開始並不想去,但團隊認為作為一個新品牌,Forbes 的曝光可以顯著提升認知度,我就同意了。拍攝那次也是我第一次化妝、第一次上鏡做那種正式棚拍。
Chamath:錢對你意味著什麼?別誤會,但你是在中年之後才變富的。到了四十多歲,錢還重要嗎?
CZ:錢當然重要,但不是全部。對我來說,有幾件事起到了作用:
第一,我確實年紀不小了。四十多歲的人,不太會像二十歲那樣追逐豪車、派對或炫耀性的消費,我對那些不感興趣。
第二,我的性格相對穩定,不太容易因外部變化而大起大落。
第三,財富增長對我來說並不是循序漸進的過程。我幾乎是從剛剛實現一點財務寬裕,直接跳到登上封面、別人說你可能是億萬富翁。但當我打開自己的錢包,數字之外的生活並沒有立刻發生什麼變化。有人跟我說「你可能已經是億萬富翁」,我反而會想真的嗎?為什麼我完全沒有這種感覺?
甚至在我們從中國搬去日本的那段時間,我還在訂經濟艙紅眼航班。後來有人提醒我應該升到商務艙,這樣能躺下睡覺,我才意識到習慣並不會因為財富骤增而自動改變。
如果一個人是階梯式變富,從 100 萬到 1000 萬,可能會買車;到 2 億可能會買遊艇,他會逐步形成一套消費與身份習慣。但我沒有經歷那樣的階梯過程,所以很多富人的習慣並沒有在我身上長出來。
Chamath:那現在呢?有時候你是億萬富翁,有時候甚至是「百億級」,這些數字到底意味著什麼?
CZ:對我而言,意義並不大。我覺得錢大致有兩層意義:
第一,保障基本生活:食物、住所、安全感。坦白說,實現這一點所需的金額並不高。人們常常會把生活複雜化,但基礎需求並不昂貴。就這層意義來說,我當然早就具備了。我生活得很舒適,但並不奢華。
第二,至於更富帶來的變化,並沒有想象中那麼大。比如我現在住的房子,客廳每隔一段時間還會漏水,因為房子很舊。外界可能以為我住得極其豪華,但事實並非如此:我住的是一個尺寸合適、位置便利、滿足家庭需要的房子。它並不新,也不講究排場,只是功能上合適。東西壞了就修,僅此而已。漏水這種事一個月前還發生過。
Chamath:這說明你務實?還是說你本身不太會被這些東西打動?
CZ:我更看重功能。能解決問題、能正常運轉,我就滿意。我不太在意裝飾、風格、顏色,也不在意閃耀的金色或類似符號性的東西。只要它好用,就夠了。
Chamath:你會有強烈的不安全感嗎?
CZ:不太會。我清楚自己的弱點,也學會了如何與之相處,我希望自己不是一個過度自負的人。
Chamath:說起來可能有些傲慢,但我確實是這兩年才開始真正了解你。我看了你從 2010 年代末到 2020 年代初的視頻,我最直接的反應,因為這也是我一直以來的挣扎,即自卑感與自負之間的拉鋸。我當時想:天哪,這個人表現得極其冷靜。看來你的情緒調節能力極強,且非常有自省意識。
CZ:他人的情緒起伏可能很大,表現為極度的喜悅或悲傷。我同樣會感到快樂或憂慮,但我的波動範圍更窄。
Chamath:這種特質讓你在很多方面都能游刃有餘。這意味著當你正埋頭解決某個難題時,所謂的「成功」在某種程度上是虛幻的,因為外人並不知道你付出的艱辛,也沒人真正關心那些枯燥的苦勞。
人們傾向於用一種簡單粗暴的方式去評斷事物,比如指著某樣東西感嘆:「哇,看你擁有的一切。」確實如此。如果你一直埋頭苦幹而沒有時間享受,其實沒有人能真正理解那種狀態。
CZ:沒錯,確實是這樣。
Chamath:好,我們聊聊 Binance 的起步。你推出了這個平台,它發展得極其迅猛,但也經歷了一些波折。你是否覺得自己在某個階段曾過度沉迷於這種增長?
CZ:我不會說我沉迷於增長,但我確實沉迷於工作。事實上,工作本身帶給我極大的滿足感和成就感。
Chamath:那時你典型的一天是怎樣的?你主要在忙些什麼?
CZ:我每天基本上要處理 20 多場會議,包括預定的電話會議或正式會談,此外還有各種瑣碎事務,還要在 Twitter 上回復用戶等等。但這讓我感到非常有意義,因為其中蘊含著一種難以言表的成就感。這種感覺並非來自金錢或增長規模。
Chamath:是什麼呢?在你執掌 Binance 期間,你是如何衡量的?有些人會死盯著滯後指標,比如營收,但營收和利潤其實是六個月甚至一年前工作的滯後體現。你最看重的領先指標是什麼?你真正關心的、能反映系統健康狀況的北極星是什麼?
CZ:我認為核心指標是日活躍用戶數,不是交易量,也不是營收。
Chamath:為什麼是日活,而不是其他指標?
CZ:這是核心所在。我認為只要你持續服務於更多用戶,你就在為他們創造價值。我堅信,當人們願意使用一個產品時,它才是有價值的。因此,使用的人越多,即便營收為零,產品依然具備價值。
任何產品都是如此,受眾越廣,價值越高,這就是我的哲學。相比之下,你可以為了短期利益去優化營收或利潤,但那樣可能會失去長期增長的潛力。我始終相信,從長遠來看,如果平台擁有龐大的用戶群,那就是價值所在——這不僅是為你自己創造價值,也是為用戶創造價值。
人們選擇使用你的平台,是因為這能為他們帶來價值。所以,這是我的「北極星指標」。除此之外,意識到有數以億計的人在使用我們的服務並從中獲益,這本身也極具意義。我的觀點是,如果用戶願意支付手續費,那一定是因為我們提供了相應的價值。
Chamath:但日活也是一把雙刃劍,因為這些活躍用戶中可能包含不法分子。你是什麼時候第一次意識到這可能成為一個嚴重問題,並必須嚴肅對待的?
CZ:實際上有一個非常清晰的時間點,那是 2018 年的元旦。當時 Binance 成立僅五個月左右,我們規模已經很大,是全球排名第一的交易平台了。當時,一名美國國土安全部的官員聯繫了我,他發來郵件請求我們協助追蹤一些黑客,這些黑客可能轉移了 Ether Delta 被盜事件的資金。
Ether Delta 是 2017 年的一家去中心化交易平台,因遭遇黑客攻擊而倒閉。那是美國政府官員第一次聯繫我們,我當時完全不知道該如何處理。我們團隊中沒有人具備與執法部門對接的經驗。於是,我召集了幾個夥伴商量:「我們要怎麼幫他?」
隨後,我們在核實其身份後,提供了他所需的信息。事後他向我們表達了感謝。我當時問他:「Joseph,你能否推薦一些具備對接執法部門經驗的人才,以便我們將來聘用?」他確實推薦了一位,但那人當時在美國,而我們那時還沒有美國實體,無法在當地雇員工,所以只能作罷。但就在那年的元旦,我意識到這種情況未來會頻繁發生。
Chamath:在那一刻你意識到,隨著使用者基數的擴大,這種事是不可避免的。
CZ:是的,這是必然的。
Chamath:即便是在使用量激增的情況下。
CZ:就在那天,我意識到我們必須聘請有執法部門工作背景的專業人士。
Chamath:那麼你後來做了什麼?
CZ:我們最終確實聘請了更多這方面的專業人才。
Chamath:顯然,你個人不會去監控每一筆交易,所以你無法察覺所有細節。但如果我們快進到後來,拜登政府對你提出的指控核心在於,像哈馬斯或其他組織在利用 Binance 進行交易,而你們的監管措施不足。
CZ:關於這一點,受限於法律協議及辯證程序等因素,我對於能說什麼和不能說什麼有嚴格的法律限制。我雖不是律師,但我會盡量避免觸及這些敏感話題。不過從宏觀角度來看,我想說拜登政府整體上對加密貨幣行業是相當敵視的,他們甚至公開向加密貨幣宣戰。因此,看到新一屆政府的態度發生了 180 度的轉變,我認為這對美國乃至全世界都是一件好事。我並不想單純指責前任政府,但我覺得他們當時確實未能理解這個行業。
Chamath:你認為他們為何表現得如此敵視?
CZ:源於對新生事物的恐懼,就這麼簡單。我想在他們的認知裡,在某種程度上是想保護現有的金融體系、銀行及相關利益方免受衝擊。此外,這些傳統行業可能也進行了大量的遊說活動,從而洗腦或影響了決策者的思維。這是人性使然,雖然並不理想,但可以理解。
Chamath:你經營著交易平台,生意蒸蒸日上。從 2018 年到 2020 年,你逐漸步入巔峰。最終,你決定開設一個美國實體。
CZ:是的,我們在 2019 年開設了 Binance.US。
Chamath:你當時為什麼覺得有必要這樣做?
CZ:2019 年當時有一些新聞,用我這個門外漢的話說,美國政府正在追擊 BitMEX。當時 BitMEX 以及 Bitfinex 的負面消息頻出。我記得波蘭政府凍結了他們大約 6 到 8 億美元的資產,而當時他們的市值也才 40 億美元左右,這是一筆巨款。
隨後,美國政府起訴他們儲備金不足。看到這些新聞後,我們意識到美國政府開始關注這個行業,我們最好進行註冊。同樣,我諮詢了許多有法律背景的朋友,普遍的共識是我們應該以合規註冊的方式在美國運營。於是在 2019 年,我們註冊了 Binance.US,它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實體,擁有獨立的部署系統、撮合引擎和流動性池。從成立第一天起,Binance.US 就一直處於監管之下。
Chamath:2019 年到 2021 年間,一切運行基本順遂。
CZ:總體來說,是的。
FTX 事件始末:與 SBF 的關係及其崩潰
Chamath:隨後你開始看到其他競爭對手異軍突起,比如 SBF 和他的 FTX 勢頭極其強勁。跟我聊聊那段經歷,你是怎麼認識他的?
CZ:我們在某個階段曾持有他們 20% 的股份,但一年後就退出了,並沒有持有太久。
我記得第一次見到他是在 2019 年 1 月,在 Binance 於新加坡組織的會議上。我記得當時 FTX 甚至還沒成立。Sam Bankman-Fried(SBF)當時還在經營 Alameda Research。他們在聖淘沙的新加坡水族館舉辦了一場酒會,還安排潛水員在魚缸裡舉著標語。
當時他們是 Binance 的 VIP 客戶,交易量非常大。所以我們和他們的關係很友好,那是 2019 年 1 月的事。幾個月後,他們找到我們,表示想建立一個期貨平台。他們提出了一個合資方案,具體細節我記不清了,但我記得他們提議的分成比例是 60/40,我們占大頭。
我當時考慮過還價,畢竟用戶都在我們手裡,他們當時還一無所有。我甚至想過提出 95/5 的分成,但我覺得那樣不太禮貌。畢竟他們依然是我們的重要交易者和 VIP 客戶,所以我們拒絕了那個提議。
Chamath:因為他們曾是流動性池中至關重要的一環。
CZ:在社交層面上我們並無太多交集,他們當時是平台的大客戶。但你要知道,當時的 Binance 也還很年輕,並非深耕多年的老牌機構,可能也就成立了半年到一年左右。後來在夏季,他們帶著更好的方案再次找到我,但我拒絕了。到了 11 月,他們第三次嘗試合作。那時 FTX 已經上線並有了一定的交易量,他們提議我們可以按這個價格轉讓 20% 的股權給你。
」那次交易涉及代幣交換,即 BNB 與 FTT 的互換,我們也因此持有了一些早期的 FTT。當時 BNB 的流動性遠高於 FTT。然而,交易達成後不久,我就開始從朋友口中聽到 SBF 在華盛頓政界和美國各處散布關於我們的負面言論。我當時覺得這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此外,他們還做了一些令人惱火的事,比如開出 5 倍的薪水,從我們這裡挖走了兩名能接觸到 VIP 數據庫的客戶經理。其中一名員工離職後,我心想,如果我們為了留住她而加薪,那就意味著要給所有人加薪 5 倍,這顯然不可行,於是她便入職了 FTX。但在她入職的第二天,我們的 VIP 客戶就開始接到他們的電話,宣稱在 FTX 交易可以獲得更優惠的費率。
於是我致電 SBF 說:「你能不能停止這種行為?我們還是你們的股東。」與此同時,他表面上還會客氣地問:「CZ,我們能不能在加密貨幣活動上一起參加個圓桌論壇?」作為投資者,我本想幫他們做推廣。事實上,我真心希望行業內能有多個成功的交易平台並存,這樣我們就不會總是成為被針對的目標。但事與願違,我不斷聽到他在背後中傷我們的消息。
到了 2021 年初,由於他們宣稱要以 320 億美元的估值融資,我們便決定退出。根據投資條款,我們對未來的融資輪次擁有否決權,如果想阻礙他們,我們完全可以動用這項權利。但我不想以此為難他們,我想的是,既然如此,不如直接退出,大家在市場上公平競爭。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交易在 2021 年 7 月最終敲定並完成了轉帳,這比他們最終爆發危機早了整整一年半。在那時,沒人能預料到後來的崩盤。
Chamath:沒錯。當時有傳言說,他們的許多問題是在你出售股份後才開始的,且兩者之間存在某種關聯,你現在的這番話有力地反駁了那種說法。
CZ:那種說法純屬無稽之談。由於業務上的競爭關係,儘管我們曾是股東,但我從未要求查閱他們的財務報表,從未開口問過。我是一個非常被動的投資者,投資後從不干預對方的經營。況且大家在期貨平台上存在競爭,所以我也刻意保持距離,讓他們自行發展。
Chamath:FTX 倒閉後,人們討論最多的幾點,一是賠付方案對部分持有現金的債權人而言並非最優;二是這些資產在後期的估值問題。回顧這一切,你認為這反映了行業的什麽現狀?
CZ:坦白說,我不了解破產清算的具體流程,也不清楚其是否公平,我只是在網上讀到了一些說法。而且為了保持透明,我必須說明 FTX 的破產管理機構目前正與我們進行訴訟,他們試圖追回一年半前我們退股時的那筆資金。因此,我目前能公開評論的內容非常有限。
我確實聽到一些中國用戶抱怨無法獲得賠償等問題。但據我所知,由於加密貨幣價格上漲,如果按美元計價,他們現在有足夠的資產進行賠償;但如果用戶當時持有的是加密貨幣,那他們本應獲得更多,我不確定具體的交易細節。
直面拜登政府「反加密」的司法部
Chamath:Binance 的情況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變得複雜的?我是指與美國政府的關係。
CZ:那是從 2021 到 2022 年間開始的,他們開始要求我們提供信息,而我們始終配合。但到了 2022 年底,形勢變得愈發嚴峻。直到 2023 年初,情況變得明朗化,我們要麼達成某種和解協議,要麼就面臨起訴。隨後便進入了漫長的幕後談判。
Chamath:作為當事人,你如何應對這種壓力?當你坐在會議室裡,聽到律師說「CZ,我想你可能會面臨刑事起訴」時,那是種什麼感覺?
CZ:首先,我沒有法律背景,所以我非常依賴專業人士的建議。那對我來說是最艱難的一段時期,因為我毫無經驗。這種事,任何經歷過一次的人都不會想再經歷第二次。我聘請了一群頂尖律師,但如何管理這些律師其實很棘手。他們雖然專業,但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專長和意見,而且每個人都想表現得自己是那個最有決策權的人。此外,律師的工作方式是極其細緻且耗時的,畢竟他們是按小時計費。
我並不是說他們不道德,他們確實想把工作做好,但往往會陷入各種細枝末節中,導致你感覺被拖向了無數個方向,那是我最苦惱的地方。我當時需要的是有人告訴我:「這就是你要關注的三件事,這就是我們要採取的策略。」由於我們的法律團隊當時還很年輕,缺乏處理此類重大案件的經驗,這讓情況變得更為複雜。
Chamath:當時你的團隊都在哪裡?
CZ:我們現在分散在世界各地。2023 年時,我大部分時間在迪拜。那段日子壓力極大。我應對壓力的方法是分析「最好」和「最壞」的情況。最好的情況: 支付罰款,簽署延期起訴協議,事情告一段落。最壞的情況: 對方試圖讓你入獄。
Chamath:那真的是最壞的情況嗎?因為當時看來,類似案例往往只是緩刑。
CZ:這確實是極端的風險。雖然之前沒人因此入獄,但他們有權提出這樣的要求。其實還有另一種「最壞情況」:如果你選擇死硬到底,拒絕協議,留在阿聯酋(阿聯酋與美國有引渡協議)。即便由於我擁有公民身份,被引渡的可能性極小,但我的旅行自由將受限。每當我跨越國境,即便那個國家沒有引渡協議,也可能存在某種政治交易。那將是一種生活在恐懼中的狀態。
Chamath:而且如果兩國是盟友,這還會導致政府間的關係變得複雜。
CZ:沒錯,這會給阿聯酋政府帶來巨大的壓力。我不希望給予我公民身份的國家添麻煩。更糟的情況是,如果你不配合,他們起訴你並發布紅色通緝令,那種生活是不堪設想的。
Chamath:你是如何解決的?
CZ:談判過程極其艱辛。在一年多的時間裡,我幾乎每天都要和 12 到 20 名隨時候命的律師開會,我們是在與拜登政府的司法部博弈。我的律師跟我說過最多的一句話是:「我們從未見過他們在處理此類案件時表現得如此敵對。」
Chamath:在某個時刻,你會對此感到麻木嗎?還是會不斷地反思,覺得「為什麼這種事會發生在我身上」?
CZ: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其中有幾個階段非常難以跨越。在談判中,當對方提出一些我們絕不能接受的條款時,你必須拒絕,即便對方寸步不讓。隨後會出現長達數周的「停滯期」。在那幾周裡,你完全不知道會發生什麼,那種感覺就像身處「煉獄」。你隨時可能被起訴,因為你已經拒絕了他們的方案。在那段時間裡,你必須在心理上做好最壞的打算:比如餘生只能待在一個國家,必須極其小心。有趣的是,兩周後,他們會主動回來詢問:「我們可以重新開始談判嗎?」
Chamath:你認為那兩周裡發生了什麼?
CZ:回想起來,我認為那是對方非常高明的談判技巧,保持沉默。對於像我這樣第一次經歷這種事的人來說,這是在拿命在博弈,而對他們來說,這是日常工作。他們很聰明,知道兩周是一個完美的博弈點。如果沉默時間太長,你就會適應那種極端壓力下的生活,反而變得無所畏懼,等他們再回來時你可能依然會說「不」。他們非常擅長這種心理戰。這種壓力是無法習慣的,它對心理是極大的挑戰。
Chamath:你最終是如何說服自己接受這些最終協議條款的?
CZ:經過多輪艱苦談判,我們最終達成了共識。我接受了關於違反《銀行保密法》的單一指控,其本質是「未能履行註冊義務」,這雖然屬於聯邦罪行且性質嚴重,但在歷史上從未有人因此被判入獄。
Chamath:這項指控聽起來更具技術性。在美國媒體的認知中,普遍認為這涉及洗錢、教唆犯罪以及未能執行 KYC 與反洗錢。大眾的認知與實際的法律指控之間是否存在關聯?它們是等同的,還是相互獨立的?
CZ:我可以試著闡述一下我的理解。首先需要聲明,我並非法律專業人士,這僅代表我作為外行人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我的理解是這樣的:第一層:違反《銀行保密法》。這是最基礎的一層,即未能履行註冊義務。Binance 在未向美國相關監管機構註冊為金融服務公司的情況下,為美國用戶提供了服務。
第二層:KYC 與 AML 程序不完備。即使公司未註冊,也應具備完善的反洗錢程序。人們往往認為合規與否是非黑即白的,但現實中它關乎執行的力度、使用的系統以及投入的人力。
第三層:明知且協助非法交易。這是更高層級的指控。如果反洗錢程序不嚴密,可能會漏掉不法分子,但這並不代表公司是故意協助。
第四層:個人直接處理非法交易。例如查理·史瑞姆為「絲綢之路」處理交易的案例。我個人從未直接處理過任何交易,這完全不在我的業務範圍內。
最終達成的共識是:Binance 未能按規註冊,且 KYC/AML 程序存在薄弱環節。對於這兩點,我們願意接受罰款並達成和解。在法律層面,僅憑這兩項指控,無其他附加罪名而在美國歷史上被判入獄的先例至今為零。然而,政府當時試圖增加兩項所謂的「加重處罰指控」(第 3 和第 4 層),聲稱我個人協助了非法交易。
Chamath:他們能否指證具體的交易記錄或證據?
CZ:不能,他們拿不出證據。他們試圖將公司層面發生的某些疏漏強加於我個人。法庭最終斷然駁回了這兩項加重指控。但在我前往美國之前,我們商定會在庭審中就此進行辯論。基於法律諮詢,我當時認為最壞的情況也不過是像 BitMEX 的 Arthur Hayes 那樣,被判處六個月的居家監禁,而他的情節(直接接觸客戶)顯然比我嚴重得多。因此我當時充滿信心,認為前往美國解決問題是最佳選擇。
Chamath:所以你的策略是承認基礎指控,並在法庭上駁回第 3、4 層指控。你抵達美國,進入法庭,隨後發生了什麼?
CZ:細節非常多。第一天是進行認罪辯護,相關條款早已由雙方龐大的律師團隊反覆推敲和琢磨。
Chamath:順便問一下,你當時住在哪裡?家人陪在你身邊嗎?
CZ:我住在西雅圖市中心的一家飯店裡。我的姐姐和母親陪著我,但我沒讓孩子來,因為他們要上學。我的合夥人還有公司要管理,而我當時已不再負責 Binance 的運營,所以我不想讓他分心。認罪辯護結束後,律師們開始就保釋條件進行辯論。我的律師認為我應該被允許返回阿聯酋等待三個月後的判決,政府則辯稱我可能會潛逃,要求我滯留美國,但承諾不會限制我在美國境內的行動。
最初,治安法官批准我返回阿聯酋,但政府隨即提起上訴。我的律師說,在他 40 年的職業生涯中,從未見過政府針對保釋條件提起上訴。他認為這種做法表現得過於激進,可能會引起法庭反感,反而對我們有利。然而結果出人意料,兩週後法庭裁定政府勝訴,我被迫滯留美國三個月。三個月期滿後,政府又申請了三個月的延期。
Chamath:在那六個月裡,你見到孩子了嗎?
CZ:沒有,我不想讓他們看到這種場面。在那段時間裡,我在美國境內旅行,或是住在姐姐家裡,盡量讓自己保持平和的心態。
Chamath:2024 年 4 月 30 日是你的宣判日。
CZ:是的。宣判前一周,政府提交了量刑建議,要求判處 36 個月監禁,這超出了所有法律指南建議上限的兩倍。與此同時,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在電視上再次向加密貨幣宣戰,並致信司法部,信中充斥著對該行業的偏見。
宣判那天,法官先是肯定了我的貢獻和为人,但隨後說出了那個轉折詞——但是。律師們在法庭上展開了激烈辯護,正是那次辯論,讓政府試圖強加給我的那兩項核心指控被法庭徹底駁回。法官確認我並未接觸過那些交易,也不知情。
聯邦監獄內部生活是什麼樣?
Chamath:所以最終判決是四個月監禁,你當時作何反應?
CZ:最初很難接受。我擔心的不是四個月的時長,而是我的個人安全。宣判後,各大媒體紛紛報導稱,我是「有史以來進入美國監獄最富有的人」。
Chamath:媒體的這種報導會讓你成為眾矢之的。
CZ:完全正確。我的律師和監獄咨詢師都警告我,如此高的知名度會讓我成為監獄裡勒索的首要目標。
Chamath:什麼是監獄咨詢師?
CZ:這是一個專業的行業,通常由前獄警或前典獄長組成。他們會教你監獄裡的生存規則:比如如何生活,如何面對挑釁。他們告訴我,如果第一天有人表現得異常友好,千萬不要接受他們的任何東西,因為這通常意味著未來要付出十倍的代價。我也諮詢了一些曾入獄服刑的人。美國的監獄系統非常龐大,關押著 200 萬人,政府每年在監獄上的投入甚至超過了教育。每個監獄都有自己的潛規則。我最終意識到,無論得到多少建議,我終究要獨自去面對這一切。
Chamath:你說你在 4 月 30 日被宣判。那麼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服刑的?
CZ:一般來說,被宣判之後,當事人並不會立刻知道自己會被送往哪裡、進入哪一所監獄。法院通常會提出兩項推薦意見,之後你會收到一封通知信。
Chamath:也就是說,你可能當時還在飯店或其他地方,等到某個日期就必須去報到,按要求入獄。
CZ:是的。但我的情況有些特殊,法官裁定我不需要接受任何形式的監管,這在同類案件中相當少見。因此我不需要按期去報到,只需要等待一封寄到我妹妹家的信——那是我向法院登記的聯繫地址。
實際上,司法部在其申請中要求對我實施「預先羈押」,也就是在香港就將我控制並帶走;我猜他們希望獲得那張「押解照片」,用於公關宣傳。
但法官明確表示:他不構成風險,不存在潛逃風險,也不會危害社會,因此沒有必要採取那種方式。法官還特別補充了一句:我不需要監管。後來我才知道,這在法律意義上很關鍵。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我服刑結束後沒有緩刑、沒有假釋,也無需接受任何監督。對我來說,這段經歷裡確實有一些出乎意料的法律細節。
Chamath:那段時間你是怎麼度過的?恐懼嗎?有沒有發生過嚴重的事情?
CZ:幸運的是,並沒有出現特別糟糕的意外。整體體驗當然非常痛苦,但沒有遭受身體傷害,也沒有捲入打鬥,更沒有遭遇真正意義上的勒索。入獄前,我的監獄顧問反覆提醒我:進去之後不要加入任何幫派,盡量保持低調,獨來獨往,少說話,不要捲入紛爭。但我走進監獄大門的第一分鐘,一個獄警就對我說:「你需要一點保護。太平洋島裔那邊在招人,你可能想加入他們。」這句話是我剛跨過門檻就聽到的。
Chamath:他是對你說的?
CZ:是的,我當時完全不明白這意味著什麼。入監的第一天流程極其繁瑣:一系列手續、脫衣搜身……之後你會被帶到你所屬的監區。那裡大概有 200 名囚犯:三排牢房,每排約 20 間,相對而立,有三層樓,底部是公共活動區。你走進去的一刻,幾乎能感受到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你身上。
後來我才意識到,監獄會按種族與族裔進行分組管理:華裔歸華裔,白人歸白人,黑人歸黑人;拉丁裔、墨西哥裔、西語系人群也會歸為一組。這樣做反而能顯著減少衝突,相近的文化與生活習慣更容易相處。
比如穆斯林囚犯有固定禮拜時間和作息,也會被安排到更便於協調的組別。獄方事實上默許並鼓勵這種分組,因為它能降低鬥毆概率。而一旦組與組之間出現摩擦,首先會在組內層級裡協調解決:如果你和其他組的人發生衝突,這就不再是個人矛盾,而是組與組的問題,會由各自的代表出面交涉。
Chamath:聽起來像工會代表。
CZ:某種程度上很像。他們會坐下來協調,說「你先退一步,我們把問題解決掉」。這背後有一整套運行機制和層級結構。只不過我在進去之前完全不知道這些。
我記得我剛到監區,一個看起來半華裔、半亞裔的人走過來對我說:「我叫 Chino,歡迎加入我們。」他用的詞是「car」。我當場愣住:我應該握手嗎?不握會不會出問題?這算不算被「拉入幫派」?當時腦子裡一團亂。那個人其實是菲律賓與德國混血。由於亞裔人數不多,監獄往往把「看起來屬於亞洲」的人都歸到同一組,甚至會把原住民、太平洋島民,包括夏威夷人也並入同一組。
在那 200 人裡,我們這個亞洲組只有 6 人。我被關進的是低安全級別監獄,按我的案件性質,本應進入更低一級的最低安全級別監獄,通常是白領犯罪者所在的區域。但因為我不是美國公民,他們把我安排在低安全級別監獄,而那裡的主要囚犯類型是毒品相關犯罪。這段經歷非常強烈,也非常荒謬,我在即將出版的書裡會詳細寫到這一部分。
Chamath:你出獄後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
CZ:好好洗個澡,吃一頓像樣的飯。監獄裡的淋浴間很小,大概就這麼一個盒子般的空間。門像西部酒吧那種半截門,只能遮住中間部分,腿和頭都露在外面。更糟糕的是,你很難在不碰到牆壁的情況下完成淋浴。出獄後的第一次洗澡,最明顯的奢侈感就是終於不必再貼著牆、在逼仄空間裡湊合。
饮食方面,水果極少,優質蛋白也極少;碳水化合物卻很多——麵包、麵粉製品、油炸食品一大堆,蔬菜很少,蛋白很少,完整的新鮮水果更是幾乎見不到。我可能好幾個月都沒見過一整顆水果。出獄後看到一盤水果,我第一反應是,這簡直是一種久違的奢侈。
Chamath:你出獄後是不是馬上就離開美國了?
CZ:我從監獄大門出來到登上飛機離開,大概只用了 26 分鐘。
Chamath:那一刻你在想什麼?你會不會覺得我能理解他們為什麼這麼做,某些部分或許合理,但也有一些明顯的過度執法讓感我到冤屈?還是你會覺得這完全是一場政治性構陷,極其不公,為什麼會發生在我身上?你當時內心的獨白是什麼?
CZ:關於認罪協議、法律條款等細節,我有一些發言限制,不能展開。
Chamath:我只是問你情緒上的感受。
CZ:從情緒上說,我只希望這一切盡快結束。並且當我剛出獄時,仍然是拜登政府時期,大選還未發生,勝負也未可知,美國政策走向仍然不明朗。
Chamath:你是 2024 年 5 月 30 日入獄的,對吧?
CZ:對。我在 2024 年 5 月 30 日入獄,四個月後,也就是 9 月 27 日完全出獄。大選在 11 月。
Chamath: By the way, at that time, you had already been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a year, and you hadn't seen your child for a year.
CZ: So my only thought at the time was to end all of this. I was also prepared that if the policy continued in its original direction, the crypto industry would continue to face sustained high pressure, and we could only survive in that environment.
Life After Leaving Binance and New Ventures
Chamath: After you returned, did you gradually come to accept the fact that you could no longer continue to manage Binance, which was also part of the plea agreement?
CZ: Yes, I later accepted it. Stepping down from a management position was very difficult, and I did cry about it. The last time I cried so hard was when my father passed away a few years ago.
But after returning to normal life for a while, I actually felt a certain degree of relief about "no longer managing Binance": I had more free time. If I had voluntarily stepped down, the outside world might say "he couldn't hold on"; b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I can't continue," which is not entirely a personal choice, at least not a narrative of "lack of energy."
And after some time, I also realized that there are many valuable and meaningful things to invest in in life. Overall, I am in a very fortunate position, with resources and enough funding to support the projects and initiatives I want to drive, such as Giggle Academy, free education, and more.
Chamath: I also want to talk about AI and these new projects. But before that, let's clarify the pardon part again: how did you start applying for a pardon, and how did you receive the pardon? What exactly did you do?
CZ: To be honest, I think almost no one really knows what the pardon process is because it doesn't seem to have a fixed process.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you need to find a lawyer to write a petition, clearly stating the arguments: why you should be pardoned, why you have been overly prosecuted, your conduct and past, etc.
Chamath: What is the essence of a pardon? Is it an acknowledgment of over prosecution?
CZ: The effect of a pardon is to restore you to a normal legal status, equivalent to erasing the previous burden. As for "why one is considered for a pardon," there can be many reasons.
Chamath: Ultimately, is it the President exercising discretion after reading the petition?
CZ: That's probably about right. The U.S. Constitution grants the President the power to pardon, and the text itself is not very detailed. As for how it actually works, it depends more on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at the time, as well as the President's personal judgment.
Chamath:换句话说,这更多地反映了当下的社会规范和政治氛围,以及总统如何解读这些因素。
CZ:我認為是的。歷史上許多總統在任期最後一天集中赦免。拜登則在任期中段就開始赦免,而且還出現了「預先赦免」。
Chamath:預先赦免確實很新穎,大概是從疫情期間開始被廣泛討論的。
CZ:他甚至給自己的兒子做過一段時間範圍的預先赦免,在一個很少被公開討論的時期。總之,在我看來,並不存在一個清晰、固定、透明的程序。總統理論上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行使赦免權。
我只知道:遞交請願之後,你就只能等待。白宮有負責赦免事務的人,我記得叫 Alice Johnson,她曾經坐過很多年牢,寫過一本很不錯的書,我讀過。
律師會不斷去問:「有沒有進展?有沒有反饋?」但往往得不到任何更新。然後某一天,事情就發生了。關於赦免流程,我所能說的也就到此為止,我懷疑外界也很少有人真正弄清它的運作機制。
Chamath:很多人會本能地想你為了拿到赦免,肯定做了些什麼,我希望你能把這件事說清楚。
CZ:我沒有做什麼,也談不上做了任何操作。但我認為,從現實角度看,如果沒有赦免,Binance 進入美國、以合規方式開展業務會非常困難。因為我是 Binance 以及 Binance US 的最終受益人,沒有赦免的話,業務在美國會受到極大限制。
如果美國想成為全球加密之都,就很難把行業裡最大的流動性池排除在外,也不可能讓美國用戶無法接觸到最大的市場與生態。而 Binance 既是最大的流動性中心之一,也是最大的加密生態之一。因此我的猜測是新總統本身是親加密的總統,他也有過被去銀行化和被針對的經驗。
Chamath:他自己談過去銀行化的感受,被系統性針對是什麼體驗。
CZ:不只是去銀行化,他還背負過 34 項刑事指控。我在獄中看電視時就看到這個消息,甚至有一項指控的細節是:他把文件帶進浴室閱讀,聽起來荒謬至極。我認為,他親身經歷了拜登司法部的強硬與激進,這種體驗可能讓他更容易產生共情。某種程度上,這也許對我獲得赦免有幫助。
Chamath:你現在如何安排自己的時間?
CZ:我依然相當忙碌。我在做 Giggle Academy,一個免費的教育平台;我也會為一些國家提供諮詢,幫助它們制定更合理的加密監管政策;我也參與投資,關注區塊鏈、AI 等方向,我們有一個很活躍的投資團隊。
Chamath:這些是在 Binance 內部做,還是外部?
CZ:在 Binance 外部,屬於 YZi Labs 的範疇。此外,我也會為 BNB Chain 生態裡的部分創業者提供輔導與支持。總的來說,事情不少。
Chamath:說說 Giggle Academy,它到底是什麼?
CZ:我的設想是教育內容完全可以被數位化,並通過移動端徹底交付。
Chamath:為什麼這件事重要?
CZ:因為現實裡有一組非常殘酷的數據,全球大約有 7 億到 8 億成年人不識字,其中三分之二是女性;此外還有大約 5 億兒童無法入學。兩者相加大約是 12 億人處在教育體系之外。
Chamath:這相當於全球人口的 12% 到 13%。
CZ:而這些人大多生活在極度貧困地區,要麼附近沒有學校,要麼負擔不起學費。即便有學校,質量也往往不理想。傳統教育體系的機制是把學生「拉齊到平均水平」:一個班那麼多人,教學進度只能照顧到「中間值」。
Chamath:那你們的軟體形態是什麼?
CZ:就是手機或平板上的一個 App。我的判斷是結合遊戲化設計、人類心理機制,以及 AI 能力,一個 App 就可以免費提供所需的教育內容。
Chamath:你看過類似 Alpha School 的模式嗎?你怎麼看?
CZ:我覺得 Alpha School 很好,做得很出色。但它成本高,難以普及到最需要的人群。
Chamath:你看過 Timeback 嗎?
CZ:我沒有深度使用過,但我見過他們的創始人和一些核心團隊。他們解決的是「讓既有教育體系變得更好」的問題;我解決的是另一個端的問題,「讓教育變得可獲得」,兩者方向不同。
Chamath:所以你的目標是盡可能大規模地傳播,你設想裡會有學校嗎?
CZ:不會,我不想做學校,我希望所有人都通過同一個 App 學習。
Chamath:我注意到你們的軟體很強調獎勵機制,徽章之類。我當時的直覺是:這像一串「麵包屑」,很容易走向代幣化、賺取激勵、支付體系……我是在過度聯想嗎?
CZ:不是,你的聯想很自然。我其實認真思考過很久,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刻意抵抗給 Giggle Academy 發代幣。確實,發行代幣有很多好處,可以做 learn-to-earn,可以激勵教師,也能激勵內容生產。但問題在於,以我的身份,一旦發行代幣,外界注意力很可能迅速從「教育」轉向「投機」:大家會去買幣、炒幣、刷任務拿幣。平台上到底是真孩子在學,還是在刷激勵,會變得難以分辨。
我希望 Giggle Academy 是真正的免費教育平台,而不是一個披著教育外衣的代幣項目。只要引入代幣,所有人都會把焦點放在代幣上。
Chamath:老實說,Giggle 聽起來很棒,但我也承認我的原始直覺就是往那個方向想了。
CZ:幾乎所有人都會這樣想,這也說明這種路徑太顯眼了,但我希望它最終被理解為教育項目,而不是加密投機項目。
Chamath:所以你的計劃是你個人持續出資,讓它擴張並普及?
CZ:原本是這樣。但後來出現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有一個社區項目通過 memecoin 的方式,向我們捐贈了大約 1200 萬美元。坦白說,到目前為止我在整個項目上大既只花了 300 萬到 400 萬美元。結果反倒變成了「錢難以花出去」:把錢花出正向影響,比想象中要難得多。
Chamath:對,帶來正向影響的花錢本質上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CZ:確實非常難。但我的計劃仍然是只要需要,我會持續資助,直到實現目標,把教育內容徹底數位化,用遊戲化、足夠黏性的方式交付給最需要的人。
Chamath:I want to bring up an AI question. You mentioned that AI is the third pillar in your life, and you see it as a massive wave-like cyclical shift. 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 about AI is that when you delve beneath the surface to a level below English, entering embedding and the embedding layer, you'll find that it's a machine-readable language, not English itself. It has a high information density, making it very suitable for intelligent agents. They can navigate within it, encrypt queries, perform tasks, and bring about a significant leap in productivity. This also means that intelligent agents will become participants in business activities, requiring a payment system. You've also mentioned that in the near future, it may become the largest user of cryptocurrency. Can you describe this vision for us?
CZ:I think the logic is actually quite straightforward. Soon, each of us will have hundreds, if not more, of intelligent agents working in the background. They will conduct transactions and allocate funds. For example, if you want to listen to this podcast, your team can charge a few cents in some business model, and of course, you can design a more complex model.
Chamath:Don't settle for just a few cents, CZ.
CZ:Of course (laughs). What I mean is, no matter which model is adopted, there will be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automated micro-payments and settlement requirements. We've discussed before that intelligent agents will buy tickets, order meals, and book hotels for us. It's not fully realized today, but it will definitely happen in the future. More importantly, the transaction frequency of intelligent agents may be a million times that of humans. They cannot accomplish all of this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banking system. The compliance processes of banks simply cannot handle this scale and speed. KYC for "intelligent agents" is logically impossible.
Chamath:And the transaction volume and frequency of intelligent agents will overwhelm traditional network systems.
CZ:Exactly, the traditional system cannot support it. For example, in terms of investment and trading, when you open a trading app today, look at the candlestick chart, click on the price, enter a value, and click the red or green button, this should not be the end state. A more reasonable interface should be "Convert 10% of your stablecoin assets into BNB." As for how to execute, large positions should be split and timed, small positions should be executed at market price directly, all of which should be automatically completed in the background, and intelligent agents can perform these operations for us.
Chamath:So, what is the most viable and realistic intelligent agent payment system today?
CZ:I'm not sure; there isn't a significantly mature system at the moment.
Chamath:Are you talking about specific crypto projects? In theory, which one might intelligent agents use?
CZ:這還很早,我不想點名任何具體項目,免得帶來不必要的價格波動。但確實有很多團隊在做,尤其最近 AI 智能體社交網絡這類概念升溫後,相關方向更熱了,我相信會逐步走到那一步。
Chamath:再問一個更宏觀的問題,當你看到很多圍繞言論自由的討論時,在加密世界裡,隱私扮演什麼角色?我對比特幣最大的疑慮之一是它缺乏可替代性,這會妨礙它達到大規模普及;同時它也缺乏隱私。很多人認為這可能是阻礙比特幣走向無所不在的最大問題。你怎麼看隱私的重要性?
CZ:我認為隱私在社會中具有基礎性地位。正如你說的,比特幣以及大多數加密貨幣的隱私能力都不足。比特幣最初被設計為假名化,但現實是鏈上的每一筆交易都可追蹤,尤其當你把中心化交易平台的 KYC 引入後,追蹤難度會進一步降低。人
們常把隱私問題簡化為「有人會用它做非法之事」,但實際上隱私有大量正當且必要的用途。舉個例子:如果你用鏈上地址支付某家飯店,外界只要知道飯店的收款地址,就可能推斷出你入住的位置,這會直接威脅人身安全。
這也是為什麼人們不會在網上公開家庭地址;在一些國家,洩露他人地址甚至屬於違法行為。當然,執法部門追查犯罪是合理需求,我並不反對。但隱私的基礎性價值仍然存在。行業未來必須認真推進隱私能力的演進,而這恰恰是當前很少有人真正投入的方向。確實有一些隱私幣,但體量和影響力都不大。
Chamath:說說你的書吧。
CZ:進展還可以,但寫書永遠比我預想的更耗時。我在獄中開始起草,只是為了讓自己有事可做,不至於一直閒著。我用一種非常簡陋的終端打字,把稿子發給助理。出獄後,我發現內容已經足夠支撐一本書,於是決定繼續完善。
但編輯極其耗時,每一輪修改都可能要兩三周。現在全書大約 9.5 萬字,差不多 300 頁,而且我同時在編輯英文版和中文版,所以周期被進一步拉長。這本書的目的,首先是把故事講清楚。外界對我、對 Binance、對整個行業有太多誤解,也存在很多負面報導。包括與政治相關的一些叙事也很複雜,這些不會成為我書裡的重點。我更希望讀者能理解我是誰、我經歷了什麼,以及從我的視角看,這家公司在某種意義上是什麼。
Chamath:這本書對你的孩子來說也很重要嗎?
CZ:我認為是重要的。孩子當然更願意站在我這一邊,他們也知道媒體敘事不全然準確,但我沒有機會用如此細緻的方式把來龍去脈完整講給他們聽。書能承載更多細節,幫助他們理解我無法在日常對話裡解釋清楚的部分。儘管書裡不能寫盡一切,但我會寫到我能寫的程度。
Chamath:你希望孩子成為什麼樣的人?
CZ:我希望他們健康、快樂,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定義人生。如果他們滿足於做一個普通人,我也完全接受;如果他們想創業、做公司,也很好;如果他們想成為藝術家,或者投身人道主義與公益事業,同樣很好。無論他們選擇什麼,我都希望自己能成為支持他們的人。
Chamath:這和你父母對你的期待像嗎?
CZ:很像。我的父母從不強迫我走某條路,他們甚至不像一些典型的中國父母那樣要求孩子必須當醫生、律師、工程師之類。他們對我的要求很樸素,不要傷害自己,也不要傷害別人;不要吸毒,不要犯罪,不要做讓別人受傷的事,僅此而已。
Chamath:我覺得很多人聽完會產生一種想法——這其實是高度讚美,如果環境不同,「那個人可能也會是我」。我們往往把成功神話化,仿佛它堅不可摧、遙不可及,是一種天降奇蹟。但並不是這樣。因為和你相處之後,我相信聽眾也能感受到,你其實就是個很普通的人。
CZ:是的,我確實是個普通人,很多人都這麼說。
Chamath:這反而有一種價值,當你做的是自己喜歡的事,時間會自然流逝。你不斷學習、不斷嘗試,抬頭一看,又有新的問題、新的方向。你能對那些心裡想著「那也許會是我」的人說幾句嗎?
CZ:當然。第一,我就是個普通人。我並不認為自己特別聰明,但成功並不需要天賦異賦。你當然不能太差,但也不必極端聰明。更重要的是原則、價值觀、情緒管理等方面。
此外,運氣也非常關鍵。對多數人來說,很多外部處境並非你能立即改變的;你能做的往往是改變自己。如果你每天推動自己一點點,不需要過度用力。逼得太狠會倦怠、會燒盡,反而走不遠。更好的節奏,是長期可持續的「略高於舒適區」的努力,比如 110% 到 130% 的投入強度,在你能堅持的前提下。如果你能堅持 30 年,再疊加一點運氣,你大概率會過得不錯,也許不會成為億萬富翁,但通常會擁有相當體面的生活。
Chamath:你覺得有必要打破一個迷思嗎,成為億萬富翁並不是人們想像的那樣?
CZ:是的,非常有必要。金錢只是人生蜘蛛網圖中的一條軸,當你達到足夠水平後,再多並不會讓你更幸福。真正影響幸福感的維度還有很多:健康、家庭、價值觀、貢獻感、正向影響,這些內在回報往往更重要。
當你錢足夠以後,更多的錢帶來的增益極低;但健康狀況如何?家人是否安好?你是否能夠自由支配時間?你是否把時間投入在真正想做的事上?你是否能與自己想在一起的人共度生活?這些都更關鍵。如果家人都健康,那已經是一份巨大的禮物。
心理健康同樣重要:如何應對壓力、保持穩定。我也很幸運,心態相對穩定。與其執著於金錢,不如在這些維度上持續提升自己。很多人只追逐金錢,卻犧牲了其他一切:拼命工作,失去自由時間,忽略家庭,健康在十年、二十年後顯著下滑。更諷刺的是,他們在追逐的過程中也並不享受,為了得到一件「得到之後也不需要那麼多」的東西,耗盡了人生。
Chamath:他們甚至連奔向目標的過程都不快樂,只是機械地耗著。
CZ:所以我其實也很感恩不再需要管理 Binance,我終於有了更多時間。過去我當然享受創業與經營,但在其他生活維度上,我做得並不好。現在我可以把精力重新分配。
Chamath:CZ,感謝你來到《All-In》播客。
CZ:謝謝邀請,很高興參與。
「原文鏈接」
猜你喜歡

巨鲸购列以太坊,引发市场震荡
Key Takeaways 近期巨鲸在以太坊价格跌破3000美元时增持,显示他们对以太坊未来的信心。 在以太坊交易所储备持续下降的背景下,持有者开始将资本从比特币转向以太坊。 短线交易者采用高买低售策略,加剧了市场价格的震荡。 以太坊网络基本面逐步改善,活跃地址数创历史新高。 资金流向和宏观环境的变化将决定以太坊价格的未来走势。 WEEX Crypto News, 26 January 2026 以太坊市场的巨鲸动态 近期,以太坊(ETH)市场出现了一系列巨鲸活动,这些活动正在引发市场广泛关注。在价格跌破3000美元大关时,一些巨鲸开始在市场上大举增持以太坊,从而对近期市场氛围和价格走势产生了显著影响。根据Lookonchain的监测数据,某个大型地址在两天内将价值约1068万美元的120个比特币兑换成3623个以太坊,此举展示了巨鲸对以太坊持久发展的信心。 巨鲸策略:积累与抛售之间的博弈 在市场参与者中,巨鲸的策略分化十分明显。一方面,一些巨鲸选择在当前价格水平上加仓以太坊,将其转入长期持有。这样做是在期待以太坊的价格在未来会上涨,让其持有的资产升值。以太坊的价格已经回吐了年初以来的涨幅,徘徊在3000美元以下,这为这些长期持有者提供了买入的机会。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巨鲸选择在当前价格走弱时抛售手中的以太坊。这些早期累积大量以太坊的持有人,通过释放筹码来进行获利了结或者资产再平衡。以太坊价格承压的背景下,这种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相互交织,使得以太坊的短期价格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波动性。…

I’m sorry, but it seems I don’t have access to the…
I’m sorry, but it seems I don’t have access to the original article content. Without specific details or…

2026年熱門加密貨幣:DOGEBALL是否是您等待的下一個1000倍加密貨幣?
重要要點 DOGEBALL項目結合了DOGE的病毒性吸引力與Layer 2的實用性,成為2026年市場上最有潛力的加密貨幣之一。 DOGEBALL的預售階段取得了驚人的增長,使用特殊代碼DB75可顯著增加代幣持有數量。 Stellar (XLM)和Hedera (HBAR)在機構層面上展現出強大的支持,為區塊鏈應用提供了穩定的基礎。 DOGEBALL的游戲化平台吸引了大量遊戲公司合作夥伴,成為未來在線遊戲中的交易層。 WEEX Crypto News, 2026-02-10 09:22:03 在2026年2月,加密貨幣市場正經歷一場「質量飛躍」。比特幣的主導地位依然穩定,而「幣季指數」(Altcoin Season Index)則顯示出重大變化。經驗豐富的交易者紛紛從投機性資產轉向擁有高實用性的基礎設施。對於尋找下一個1000倍潛力加密貨幣的人來說,目前的市場整合階段提供了一個進入高潛力項目的稀有窗口,這些項目尚未進入主流交易所。在這個市場變動之際,DOGEBALL項目正在與其社群慶祝,提供一項戰略優勢,遠遠超過典型的市場收益。 DOGEBALL為何具備成為下一個1000倍加密貨幣的位置 DOGEBALL是DOGECHAIN的原生實用代幣,DOGECHAIN是一個世界首創的,專為全球遊戲產業設計的以太坊Layer…

HBAR作為2026年全球重置「隱形管道」的角色
Hedera正在穩步成為機器驅動的全球經濟的「隱形管道」,這一轉型於2026年的世界經濟論壇中得到了強調。 Hedera的HBAR被視為支撐現實世界金融和數據基礎設施的企業效用代幣,與高波動性的零售投資相對。 HBAR網路至今已超過710億筆交易,網路費用增長約800%,但仍遠低於以太坊或Solana。 在機構層面,Hedera引領「現實世界資產」的發展,並參與CBDC和人工智慧驅動的商業模式實驗。 WEEX Crypto News, 2026-02-10 09:22:02 隨著新興經濟格局的演變,Hedera Hashgraph正迅速成為被稱為「隱形管道」的全球經濟基礎。根據加密貨幣研究者Cheeky Crypto的研究分析,該網路的設計旨在讓用戶在不知不覺中使用,即使在全球重置的2026年也不例外。這項創新的進步將幫助Hedera在機器驅動經濟中的地位日益強化。 Davos 2026的贊助者角色和710億筆交易 當許多散戶交易者仍在熱衷於追逐迷因幣和高波動投機交易時,HBAR則被塑造成一個企業級的效用代幣。這讓Hedera的技術在Davos 2026中引起廣泛關注。在活動期間,Hedera作為美國館的主要贊助商之一,與微軟和輝瑞等大公司一道受到尊重。與此同時,在一次CNBC的訪談中,Hedera的領導層將重點放在下一階段人類文明所需的信任基礎設施,而不是零售加密貨幣的話題。 視覺展示強調Hedera的治理委員會,由39個組織組成,包括谷歌、IBM、戴爾、T-Mobile等,被描述為圍繞HBAR生態系統的「保護環」。這些組織的輪換制度被認為是一種故意的治理選擇,旨在分散權力並保持觀點的多樣性,如波音和倫敦大學學院於2025至2026年期間輪替,並有像Repsol這樣的新成員加入。 在網上活動方面,HBAR的交易量超過710億筆,該數據與傳統區塊鏈的交易量形成鮮明對比,突顯出其高效能和現實應用。Hedera共識服務費用上升約800%(從每筆$0.0001升至$0.0008),但仍維持在每筆交易的很小成本內,分析師表示其費用調整是為了支持節點運營者的可持續性。…

現在最佳投資的加密貨幣:Pepeto 與 Solana 和 Hedera 一同進入聚光燈,潛力無限
Pepeto 正在與其他頂級加密貨幣如 Solana 和 Hedera 一起引起投資者的廣泛關注,其未來潛力被廣泛看好。 與業界知名的加密貨幣相比,Pepeto 擁有獨特的技術優勢與市場機會。 加密貨幣市場的快速發展為新興幣種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和創新契機。 為了理解 Pepeto 的市場潛力,需要深入分析其技術基礎及市場定位。 WEEX Crypto News, 2026-02-10 09:22:05 爭相投資的加密新星:Pepeto…

Solana 價格預測:SOL 夜間反彈12% – 但這一信號可能破壞一切
關鍵要點 Solana 價格在短期內反彈12%,但某一重要信號可能引發價格下滑。 長期持有者對 Solana 失去信心,持倉數據顯示增持速度顯著減慢。 如果目前的短期支撐失守,Solana 可能下探至70美元的重要關口。 更多投資者開始關注如 SUBBD 等具有實際應用的平台,該平台已獲得150萬美元的預售資金支持。 WEEX Crypto News, 2026-02-10 09:24:03 隨著加密市場的快速變化,Solana 當日上演了一場嘹亮的反彈,拉升幅度達到12%。這次的價格波動讓許多投資者歡呼雀躍,但在一片欣喜之中,資深分析師卻對未來走勢表示擔憂。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一個看似積極的信號隱含著潛在的風險?本文將深入探討。…

比特幣價格預測:中本聰的錢包剛收到 17.4 萬美元的 BTC – 創始者是否即將回歸?
重點提要 神秘的比特幣轉帳引發市場猜測,中本聰錢包的動作再次讓市場關注。 如果中本聰復出,可能對市場造成顛覆性的影響,甚至引起恐慌性拋售。 比特幣當前的技術阻力位在 70K 美元以上,而支持位則在 60K 美元附近。 新的比特幣預售採用了 Solana 技術以提升比特幣的交易速度和擴展性。 長期來看,比特幣的持久價值依賴於其基礎設施的實用性。 WEEX Crypto News, 2026-02-10 09:24:05 比特幣世界再次被震動,一筆出人意料的交易轉入與中本聰有關的傳奇錢包,引發社群對於比特幣創始人可能復出的狂熱討論。這次突然的轉帳來自一個尚不知名的錢包,涉及2.56枚比特幣,約合17.6萬美元,這一事件立即引起了市場的大量揣測和不安,彷彿中本聰本人可能從長達十五年的沉寂中再次出現。…

當下最佳加密貨幣投資選擇 - XRP、比特幣、以太坊
各大加密貨幣在近期的跌勢後,正準備迎接下一波牛市。 美國《加密貨幣清晰法案》是業界關注的焦點,旨在為加密貨幣企業提供明確的立法指南。 XRP 以其快速且低成本的跨境轉帳能力,在全球金融體系中佔有一席之地。 比特幣和以太坊仍然在大型機構與散戶投資者中擁有重要地位,並潛力成長。 WEEX Crypto News, 2026-02-10 09:24:05 加密貨幣市場近期經歷了一段持續的拋售行情,使得比特幣價格一度跌落至七萬美元以下。然而,隨著市場的調整與重組,業界已開始為下一波牛市做好準備。其中的焦點之一即是美國的《加密貨幣清晰法案》,該法案將為美國加密貨幣企業提供明確的法律指南。儘管政策制定者與銀行業之間的意見分歧,導致法案的推遲,但全球加密貨幣正持續融合至全球金融基礎設施中。 XRP (XRP):興起的新策略,衝擊SWIFT系統的可能性 XRP作為一種具有強大市場佔有率(市值達到850億美元)的加密貨幣,其快速且低成本的國際轉帳能力使其在區塊鏈支付領域中備受推崇。XRP的台上推手——Ripple,透過構築XRP Ledger(XRPL)為金融機構提供一種更具成本效益的跨境支付替代方案,以撼動以往緩慢且昂貴的SWIFT系統。 Ripple最近推出了一項計畫,旨在將傳統金融(TradFi)帶入鏈上世界,並藉助XRP代幣來實現機構級支付和代幣化(Tokenization)的基礎設施建設。諸如聯合國資本發展基金和白宮等知名組織曾讚揚XRP的高效性,強化了它在全球金融對話中的重要性。 自2020年打贏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關於XRP未經許可銷售的訴訟後,XRP在2025年中期達到了3.65美元的歷史新高。然而,由於市場風險偏好轉向,XRP的價格回落至約1.43美元。美國監管機構最近批准了XRP現貨交易所交易基金(ETF),這將讓機構投資者和散戶透過受監管的金融工具進行投資。隨著更多ETF產品的推出和監管清晰性的增加,XRP有可能在第二季度末達到5美元。 比特幣…

中國阿里巴巴AI預測到2026年底XRP、Solana和比特幣的價格
阿里巴巴人工智慧模型KIMI對XRP、Solana和比特幣的未來價格給出了激進的預測,預計這些數字資產將創下新高。 Ripple的XRP有潛力在未來幾年內達到10美元,這取決於其技術指標和市場情況。 Solana的價格可能攀升至400美元,隨著該網絡的使用逐漸增加,預期有大量機構需求。 比特幣的潛在價格範圍巨大,有可能達到甚至超過半百萬美元,受限於供應及增長的機構參與。 WEEX Crypto News, 2026-02-10 09:24:04 過去十年來,隨著技術和金融領域的迅速發展,數字貨幣逐漸成為投資者眼中新興的重要資產類別。如今,數字資產的價格動向成為許多投資者關注的焦點。中國的阿里巴巴集團推出的一款名為KIMI的人工智慧模型,以其對未來幾年主要數字貨幣——主要是XRP、Solana和比特幣的預測而聞名。這些預測反映了數字貨幣可能的成長路徑及其在市場上的潛力。儘管市場充滿不確定性,但這些評估卻提供了一定的見解和參考。 XRP ($XRP):阿里巴巴AI為其價格目標畫下一條清晰的上升道路 Ripple公司的XRP一直以其在機構級跨境支付中的應用而受到廣泛關注。根據KIMI模型的預測,如果市場情況持續樂觀,XRP的價格有望在2026年底前達到10美元。考量到當前的交易價格約為1.45美元,這將意味着潛在的漲幅達到大約600%。 技術上來看,XRP的相對強弱指數(RSI)接近30,顯示該資產目前接近被超賣的範圍,這通常預示著賣壓將達頂峰,購買者可能會在此價格水平入市以把握交易機會。 除了技術指標,從2025年末到2026年初的支撐和阻力線區形成的看漲旗形圖案,也似乎預示著上漲趨勢的可能性。此外,來自已獲美國批准的XRP交易所交易基金的機構資金流入、Ripple日益增長的合作夥伴網絡以及今年可能最終確定的「美國薪資透明法案」都被視為可能推動XRP達到KIMI模型目標的催化劑。 Solana (SOL):阿里巴巴AI看好SOL達到400美元 Solana作為一個高速且低費的公鏈平台,已經吸引到大量的市場關注。根據目前的數據,Solana網絡託管的總鎖定價值(TVL)達到約64億美元,市值也接近500億美元。由於網絡使用量的穩定增長,以及開發者和用戶的高水平參與,SOL一直受到投資者的青睞。…

委內瑞拉的反腐調查對加密貨幣產業的影響:交易所和礦場被關閉
委內瑞拉進行反腐調查,涉及國有石油公司與加密貨幣管理部門合作,導致多名官員被捕。 SUNACRIP重組,導致國內眾多礦場被迫暫停運行,對應之未來政策走向尚不明確。 雖然部分加密貨幣交易所受到關閉命令,但情況和解釋不一,市場疑雲重重。 幾位高級官員和商業人士因涉嫌腐敗被拘留,調查可能導致進一步逮捕行動。 WEEX Crypto News, 2026-02-10 09:24:05 在全球加密貨幣市場動盪不安的背景下,委內瑞拉的舉措無疑增加了不確定性。最近,委內瑞拉政府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反腐敗運動,這場運動的矛頭直指加密貨幣行業和與其相關的多個政商要員。儘管反腐是必要之舉,但在加密貨幣行業,尤其是在已經陷入困境的委內瑞拉經濟中,加密行業被迫關閉其實施過程仍令人憂心。 加密貨幣行業受重創 委內瑞拉的許多加密相關企業近期接到指令,要求暫停運作。隨著國家總統下令重組加密貨幣監管機構,影響涉及多家交易所和礦場。這一突如其來的政策變動引發了業內恐慌,尤其是在工業重地如玻利瓦爾州,這一政策決定被視為與私營業者利益相悖。玻利瓦爾、拉臘和卡拉博波等州皆有礦場遭到停產,這一情形在全國範圍內屢見不鮮。 能源供應商CORPOELEC下令在調查期間全國關閉雜點設施,這對國內的載能設施而言可謂重大打擊。雖然目前還無法核實究竟有多少礦場已被關閉,然而有報導指出,許多持牌礦場也未能倖免,且其關閉不僅帶來了裁員風險,還影響了賦稅。 交易所的疑雲 除礦場外,委內瑞拉的交易所也成為受害者。多份報導顯示,該國的一些交易所被要求停止運作。其中,初創公司Cryptobuyer在推文中表示,由於SUNACRIP整頓過程以及依規行事,包括Cryptobuyer在內的多家公司被迫關閉。然而,事情在一天後出現反轉,SUNACRIP於推特聲稱,從未下令停止運營,並對交易所繼續運營表示支持。此類互相矛盾的聲明讓人摸不著頭腦,Cryptobuyer則將矛頭反指向部分媒體過度詮釋。 委內瑞拉律師Ana Ojeda Caracas指出,這些措施屬於“暫時性”,但SUNACRIP至今未對外界的不明確性作出官方澄清。加密貨幣全國協會也表示,私營公司不應為監管機構內部的問題擔責,他們計畫針對新任機構負責人Anabel…

為什麼加密貨幣今日上漲?– 2025年10月2日
加密貨幣市值上漲4.2%,總市值達到4.17兆美元。 前100名加密貨幣中有98種在過去24小時上漲。 比特幣(BTC)上漲3.7%,交易價格為118,682美元。 乙太坊(ETH)上漲6.3%,交易價格為4,399美元。 Dogecoin(DOGE)成為表現最佳的加密貨幣,上漲9.7%。 WEEX Crypto News, 2026-02-10 09:26:06 加密貨幣市場在2025年10月2日迎來一波整體上漲,加密貨幣市值增長了4.2%,目前總市值達到4.17兆美元。這次的上漲大幅超過最近的平均水平,特別是前100名加密貨幣中,有98種在過去24小時內呈現上升趨勢。與此同時,整個加密貨幣市場的交易量達到2150億美元,表現強勁。 加密貨幣的贏家與輸家 目前,前十大市值加密貨幣中的所有項目在過去24小時內全部上漲。 比特幣和乙太坊強勢表現 比特幣(BTC) 上漲了3.7%,目前交易價格為118,682美元。而 乙太坊(ETH) 的表現更為亮眼,上漲了6.3%,目前價格定格在4,399美元,成為當日表現最佳的加密貨幣之一。乙太坊持續的優秀表現再次鞏固了其在市場中的地位。…

聯準會沃勒表示隨著傳統金融的介入,虛擬貨幣的熱潮正在消退
主要摘要 聯準會官員沃勒指出,虛擬貨幣的波動性是市場的本質,價格上上下下屬正常現象。 傳統金融的介入可能對虛擬貨幣市場的近期下跌造成影響。 沃勒認為美國國會未及時通過虛擬貨幣市場結構法案,加劇了市場的不確定性。 沃勒透露聯準會今年將推行「瘦身主帳戶」,以便創新支付公司使用。 他強調支付帳戶有助於支付系統的創新,同時保持安全。 WEEX Crypto News, 2026-02-10 09:26:05(today’s date,foramt: day, month, year) 虛擬貨幣市場的本質與背景 聯準會理事克里斯·沃勒(Chris Waller)對於虛擬貨幣近期市場況狀進行了評估和分析。他提到,虛擬貨幣市場的大幅波動實際上是這個領域的一部分,是其運作的自然週期。他進一步指出,隨著傳統金融機構增加參與,加上相關法規的缺失,這種波動更被放大。…

Post-Quantum qONE 超流動代幣售罄,24 小時內募得 95 萬美元
重要重點 qONE 代幣在公開預售中成功募得 95 萬美元,展示出 Post-Quantum Cryptography(後量子密碼學)解決方案的高需求。 qONE 是首個在 Hyperliquid 上推出的量子抗性代幣,其發行由 qLABS 及加拿大公司 01 Quantum 聯合研發的量子防禦技術所支撐。 qONE 的技術優勢在於其兼容現有鏈,並利用…

BTC交易員等待50K底部:本週了解的五件事
主要收穫 本週比特幣價格預測顯示更低的宏觀低點可能即將到來。 美國通脹數據及日本驅動的貨幣波動讓市場參與者更加謹慎。 美元強勁可能成為比特幣市場潛在波動催化劑。 日本新財政政策時代對加密貨幣的短期影響待觀察。 比特幣礦工大量將BTC轉移至交易所,可能影響短期價格走勢。 WEEX Crypto News, 2026-02-10 09:26:05 隨著二月第二週的開端,比特幣(BTC)仍處於防禦狀態,交易員們逐漸調整預期,認為在強勁的下跌後,BTC可能會進一步回撤到60000美元或甚至50000美元,才能夠形成持久的宏觀底部。 比特幣價格預期嘗試60000美元的再測試 儘管比特幣目前仍在70000美元以上交易,但短期內的價格走勢卻不是特別樂觀。根據TradingView的數據顯示,BTC/USD在每週收盤時的波動性不足,與上週15個月低點相比高出約20%。 交易員CrypNuevo在一篇X上的主題中警告,目前的反彈可能只是為了清算晚些時候的短倉頭寸所做的操控性舉動。他強調,價格向上推動的意圖主要是為了打擊存在於72000美元至77000美元之間的短倉清算。「我們真正期待的是在接下來的每週K線中至少填補50%的長影線。」CrypNuevo暗示,短期內可能會有部分底部再測試。 美國通脹數據來臨,聯儲政策緊張浮現 本週的宏觀焦點回到美國通脹數據上,尤其是預期於週五發布的1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這將跟隨多項美國就業數據釋出。再者,新任聯邦儲備理事會主席的提名更為市場帶來不安。Kevin Warsh的提名被認為對於放寬金融條件持反對意見,這對風險資產表現帶來了不小壓力。…

XRP 價格預測:13 年前的文章證明 XRP 一直優於比特幣 —— 為什麼被隱藏了?
比爾·摩根(Bill Morgan)認為 Ripple 實際上的潛力被故意壓制,長期以來的故事被人為構建的敘述掩蓋。 根據摩根的說法,XRP 自 2013 年以來的早期樂觀評價被刻意淡化,部分官方紀錄中涉及它的內容遭到刪減。 XRP 價格目前在下降趨勢中,不過仍存在短期支撐,未來需要突破關鍵阻力位才能轉向牛市。 加密貨幣市場不總是獎勵技術最優者,而是更傾向於獎勵那些能夠抓住市場注意力的項目。 WEEX Crypto News, 2026-02-10 09:26:06 Ripple 是否被故意推至幕後?…

比特幣熊市尚未結束?交易員預測BTC價格“真實底部”在5萬美元
Key Takeaways 一些交易員對比特幣近期反彈行情持懷疑態度,預測新的宏觀低點可能會發生。 雖然比特幣當前價格在7萬美元左右,但與2022年熊市相比的分析卻表明修正尚未結束。 比特幣的移動平均線及美國現貨比特幣ETF的成本基礎成為關注焦點。 不確定2022年的市場走勢會完全重演,市場未來走向仍待觀察。 WEEX Crypto News, 2026-02-10 09:28:06 比特幣市場分析及未來走勢 最近,關於比特幣市場的未來走勢引發了廣泛討論。一些資深交易員和分析師指出,儘管在上週末比特幣(BTC)價格上升了多達3%,但這並不構成熊市結束的標誌。對於持久的熊市形勢,他們提醒投資者可能會迎來新的宏觀低點。分析顯示,即使比特幣價格一度突破71,000美元,相較於上週五的15個月低點上漲了20%,投資者對於反彈的持續性依然保持懷疑。 著名獨立分析師Filbfilb在社群上分享了比特幣當前價格走勢與2022年熊市的比較圖,並指出,50周指數移動平均線(EMA)仍然顯示出不易樂觀的跡象。Filbfilb表示,市場尚未看到最終的拋售現象,這意味著比特幣價格可能會下降到5萬美元以下,這是ETF買入者多數會相對虧損的水準。 另一位分析師Tony Severino也持類似觀點,使用多個價格指標做出預測,認為新低點幾乎是必然的。這顯示市場的懷疑情緒很強,尤其是在未來可能出現的新變化。 市場技術分析與支持區間 除了持續的熊市特徵之外,不少分析家還提及了200周簡單移動平均線(SMA)及指數移動平均線作為比特幣的支撐區域,這一區間落在58,000到68,000美元之間。Caleb…

聯準會投入「逐步印鈔」模式——Lyn Alden的觀察
文章要點 聯準會已進入「逐步印鈔」時代,資產價格將輕微受到刺激。 調整利率政策對加密貨幣價格有重大影響,高利率可能導致經濟放緩。 Kevin Warsh被提名為聯準會主席,市場憂慮其更偏向加息。 謠言四起,市場對2026年的利率政策方向感到不確定。 WEEX Crypto News, 2026-02-10 09:28:06 美國聯邦儲備系統(聯準會)現正進入一個「逐步印鈔」的時代,據比特幣支持者兼經濟學家和Lyn Alden指出,這種貨幣政策將只會在輕微程度上刺激資產價格,並不會如比特幣圈中許多人所預期的那樣劇烈。Alden在她的投資策略通訊中表示,她的基本預測大致符合聯準會的預期,即資產負債表將按與銀行總資產或名義GDP相同的比例增長。 根據Alden的見解,價值儲存資產如比特幣可能會持續被投資者青睞,尤其是在避免過度投機的情況下,她傾向於將投資重心從過熱市場轉向被低估的區域。她強調這種策略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聯準會政策可能帶來不確定性的時期。 特朗普政府提名Kevin Warsh為下一任聯準會主席引發市場強烈反響。許多市場觀察者認為,Warsh較其他候選人更傾向於加息,此舉令投資者對未來利率政策充滿焦慮。利率政策一直是影響經濟活動及加密貨幣市場的重要因子。一方面,於市場上增加信貸供應可被視為利好各類資產;另一方面,提高利率則通常會導致經濟放緩及資產價格下跌的風險。 聯準會議上的市場預期 目前市場上對於三月即將舉行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會議持審慎態度。根據C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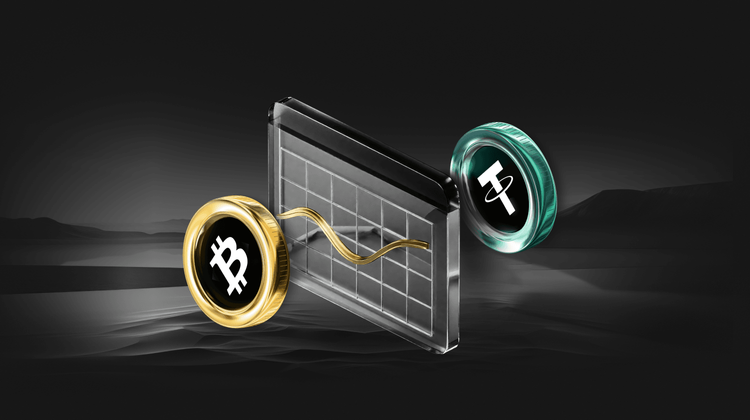
預測市場:新型公開來源情報技術
關鍵要點 預測市場因資訊透明而成為國際情報的開放來源。 加密貨幣市場透過公開紀錄揭示美國的機密活動。 高度透明的平台使外國情報機構能夠追蹤機密洩漏跡象。 司法部的政策變化加劇了監管的盲點,尤其是在數位資產方面。 在這個新時代,crypto專家可能成為最有價值的情報資產。 WEEX Crypto News, 2026-02-10 09:28:06 在當今數位化的世界中,傳統的情報手段正在經歷一場巨大變革。預測市場正成為一種新的公開來源情報技術,喚起了國際情報界的廣泛關注。這些市場不僅可以讓人們賭博美國未來的政治舉措,甚至在無意中揭露了高度機密的國家行動。當每一筆交易被永久地刻錄在區塊鏈上,訊號不再依賴於肉眼難見的線索,而是成為國際利益競爭中的重要棋子。 洩漏與逆轉的絕佳示例 2025年10月,加密貨幣市場出現了一次令人不安的震動。就在特朗普總統宣布意外關稅政策的前一小時,一名交易者突然拋售了大量比特幣和以太幣的空頭頭寸,從而獲得了接近九位數的收益。這一操作引發了市場的激烈討論,並讓人們將其稱為「特朗普內線鯨」的一個例子。而到了2026年初,一個匿名的Polymarket賬戶,在捕獲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的行動前數日,就投入了數萬元的賭注。結果不久後,隨著馬杜羅被捕,這些頭寸得到了數十萬美元的回報。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預測市場並不干預交易的合法性,也無法追蹤交易背後的訊息來源。這些市場運作如同中立的場地,僅記錄信念與資金流向,與其合法性無關。當司法部的行動政策發生反轉時,這一結構性問題的影響變得更加明顯。 預測市場作為公開來源信號 預測市場允許用戶對世界各地即將發生的事件進行賭注,從競選選舉、法院判決到戰爭狀況,甚至某些領導人的命運。由於加密貨幣的介入,每一筆賭注都被永久的記錄在區塊鏈上。例如,高流動性的衍生品平臺如Hyperliquid,提供了價格變動的平行渠道,讓交易者能夠透過多頭和空頭頭寸表達其內部消息。 對於外國情報機構而言,這些是具有完美記憶的信念市場,非常適合進行數據挖掘。假如某個新錢包出現且其交易時機總是與敏感地緣政治事件相關聯,那麼該錢包不再只是交易者,而是一種信號。在傳統市場中,很大部分行為因暗池、場外交易流量及延遲報告而被掩蓋,但在區塊鏈上卻因其設計的極度透明而無所遁形。…
巨鲸购列以太坊,引发市场震荡
Key Takeaways 近期巨鲸在以太坊价格跌破3000美元时增持,显示他们对以太坊未来的信心。 在以太坊交易所储备持续下降的背景下,持有者开始将资本从比特币转向以太坊。 短线交易者采用高买低售策略,加剧了市场价格的震荡。 以太坊网络基本面逐步改善,活跃地址数创历史新高。 资金流向和宏观环境的变化将决定以太坊价格的未来走势。 WEEX Crypto News, 26 January 2026 以太坊市场的巨鲸动态 近期,以太坊(ETH)市场出现了一系列巨鲸活动,这些活动正在引发市场广泛关注。在价格跌破3000美元大关时,一些巨鲸开始在市场上大举增持以太坊,从而对近期市场氛围和价格走势产生了显著影响。根据Lookonchain的监测数据,某个大型地址在两天内将价值约1068万美元的120个比特币兑换成3623个以太坊,此举展示了巨鲸对以太坊持久发展的信心。 巨鲸策略:积累与抛售之间的博弈 在市场参与者中,巨鲸的策略分化十分明显。一方面,一些巨鲸选择在当前价格水平上加仓以太坊,将其转入长期持有。这样做是在期待以太坊的价格在未来会上涨,让其持有的资产升值。以太坊的价格已经回吐了年初以来的涨幅,徘徊在3000美元以下,这为这些长期持有者提供了买入的机会。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巨鲸选择在当前价格走弱时抛售手中的以太坊。这些早期累积大量以太坊的持有人,通过释放筹码来进行获利了结或者资产再平衡。以太坊价格承压的背景下,这种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相互交织,使得以太坊的短期价格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波动性。…
I’m sorry, but it seems I don’t have access to the…
I’m sorry, but it seems I don’t have access to the original article content. Without specific details or…
2026年熱門加密貨幣:DOGEBALL是否是您等待的下一個1000倍加密貨幣?
重要要點 DOGEBALL項目結合了DOGE的病毒性吸引力與Layer 2的實用性,成為2026年市場上最有潛力的加密貨幣之一。 DOGEBALL的預售階段取得了驚人的增長,使用特殊代碼DB75可顯著增加代幣持有數量。 Stellar (XLM)和Hedera (HBAR)在機構層面上展現出強大的支持,為區塊鏈應用提供了穩定的基礎。 DOGEBALL的游戲化平台吸引了大量遊戲公司合作夥伴,成為未來在線遊戲中的交易層。 WEEX Crypto News, 2026-02-10 09:22:03 在2026年2月,加密貨幣市場正經歷一場「質量飛躍」。比特幣的主導地位依然穩定,而「幣季指數」(Altcoin Season Index)則顯示出重大變化。經驗豐富的交易者紛紛從投機性資產轉向擁有高實用性的基礎設施。對於尋找下一個1000倍潛力加密貨幣的人來說,目前的市場整合階段提供了一個進入高潛力項目的稀有窗口,這些項目尚未進入主流交易所。在這個市場變動之際,DOGEBALL項目正在與其社群慶祝,提供一項戰略優勢,遠遠超過典型的市場收益。 DOGEBALL為何具備成為下一個1000倍加密貨幣的位置 DOGEBALL是DOGECHAIN的原生實用代幣,DOGECHAIN是一個世界首創的,專為全球遊戲產業設計的以太坊Layer…
HBAR作為2026年全球重置「隱形管道」的角色
Hedera正在穩步成為機器驅動的全球經濟的「隱形管道」,這一轉型於2026年的世界經濟論壇中得到了強調。 Hedera的HBAR被視為支撐現實世界金融和數據基礎設施的企業效用代幣,與高波動性的零售投資相對。 HBAR網路至今已超過710億筆交易,網路費用增長約800%,但仍遠低於以太坊或Solana。 在機構層面,Hedera引領「現實世界資產」的發展,並參與CBDC和人工智慧驅動的商業模式實驗。 WEEX Crypto News, 2026-02-10 09:22:02 隨著新興經濟格局的演變,Hedera Hashgraph正迅速成為被稱為「隱形管道」的全球經濟基礎。根據加密貨幣研究者Cheeky Crypto的研究分析,該網路的設計旨在讓用戶在不知不覺中使用,即使在全球重置的2026年也不例外。這項創新的進步將幫助Hedera在機器驅動經濟中的地位日益強化。 Davos 2026的贊助者角色和710億筆交易 當許多散戶交易者仍在熱衷於追逐迷因幣和高波動投機交易時,HBAR則被塑造成一個企業級的效用代幣。這讓Hedera的技術在Davos 2026中引起廣泛關注。在活動期間,Hedera作為美國館的主要贊助商之一,與微軟和輝瑞等大公司一道受到尊重。與此同時,在一次CNBC的訪談中,Hedera的領導層將重點放在下一階段人類文明所需的信任基礎設施,而不是零售加密貨幣的話題。 視覺展示強調Hedera的治理委員會,由39個組織組成,包括谷歌、IBM、戴爾、T-Mobile等,被描述為圍繞HBAR生態系統的「保護環」。這些組織的輪換制度被認為是一種故意的治理選擇,旨在分散權力並保持觀點的多樣性,如波音和倫敦大學學院於2025至2026年期間輪替,並有像Repsol這樣的新成員加入。 在網上活動方面,HBAR的交易量超過710億筆,該數據與傳統區塊鏈的交易量形成鮮明對比,突顯出其高效能和現實應用。Hedera共識服務費用上升約800%(從每筆$0.0001升至$0.0008),但仍維持在每筆交易的很小成本內,分析師表示其費用調整是為了支持節點運營者的可持續性。…
現在最佳投資的加密貨幣:Pepeto 與 Solana 和 Hedera 一同進入聚光燈,潛力無限
Pepeto 正在與其他頂級加密貨幣如 Solana 和 Hedera 一起引起投資者的廣泛關注,其未來潛力被廣泛看好。 與業界知名的加密貨幣相比,Pepeto 擁有獨特的技術優勢與市場機會。 加密貨幣市場的快速發展為新興幣種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和創新契機。 為了理解 Pepeto 的市場潛力,需要深入分析其技術基礎及市場定位。 WEEX Crypto News, 2026-02-10 09:22:05 爭相投資的加密新星:Pepeto…
Solana 價格預測:SOL 夜間反彈12% – 但這一信號可能破壞一切
關鍵要點 Solana 價格在短期內反彈12%,但某一重要信號可能引發價格下滑。 長期持有者對 Solana 失去信心,持倉數據顯示增持速度顯著減慢。 如果目前的短期支撐失守,Solana 可能下探至70美元的重要關口。 更多投資者開始關注如 SUBBD 等具有實際應用的平台,該平台已獲得150萬美元的預售資金支持。 WEEX Crypto News, 2026-02-10 09:24:03 隨著加密市場的快速變化,Solana 當日上演了一場嘹亮的反彈,拉升幅度達到12%。這次的價格波動讓許多投資者歡呼雀躍,但在一片欣喜之中,資深分析師卻對未來走勢表示擔憂。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一個看似積極的信號隱含著潛在的風險?本文將深入探討。…
